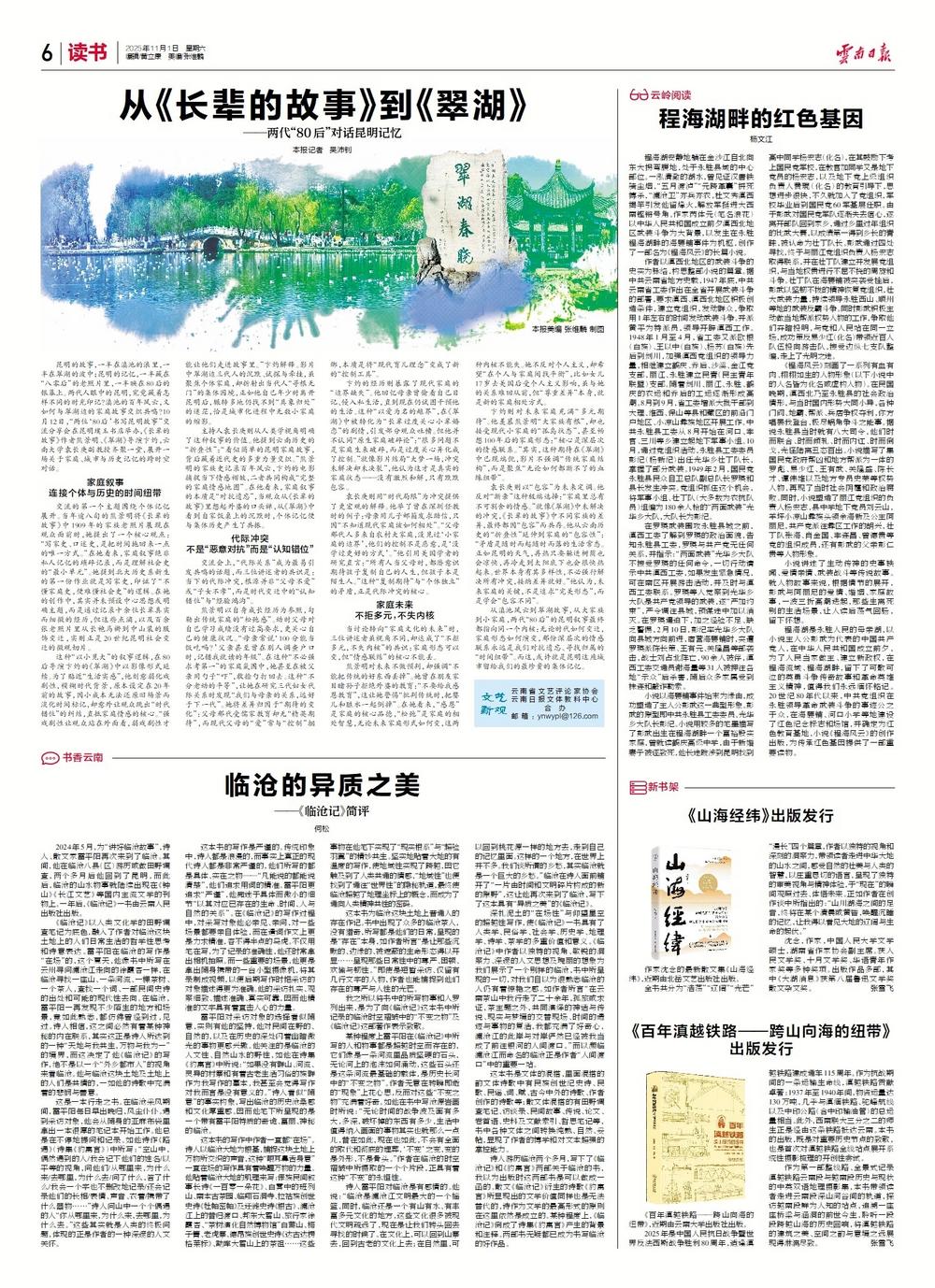何松
2024年5月,为“讲好临沧故事”,诗人、散文家雷平阳再次来到了临沧。其间,他在临沧八县(区)游历或做田野调查,两个多月后他回到了昆明,而此后,临沧的山水物事就陆续出现在《钟山》《长江文艺》等国内主流文学的刊物上。一年后,《临沧记》一书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临沧记》以人类文化学的田野调查笔记为底色,融入了作者对临沧这块土地上的人们日常生活的哲学性思考和诗意表达。雷平阳在临沧的写作是“在场”的,这个夏天,他像书中所写在云州寻问澜沧江走向的徐霞客一样,在临沧寻找一座山、一条河流、一棵茶树、一个茶人,查找一个词、一部民间史诗的出处和可能的现代性去向。在临沧,雷平阳一再发现不少陌生的地方和场景,竟如此熟悉,都仿佛曾经到过,见过。诗人相信,这之间必然有着某种神秘的内在联系,其实这正是诗人所达到的一种“天地与我共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而这决定了他《临沧记》的写作,绝不是以一个“外乡都市人”的视角来看临沧。他与临沧这块土地及土地上的人们是共情的,一如他的诗歌中充满着的悲悯与善意。
这是一本行走之书。在临沧采风期间,雷平阳每日早出晚归,风尘仆仆。遇到采访对象,他会从随身的亚麻布袋里拿出一本很厚的笔记本开始工作。他总是在不停地提问和记录。如他诗作《路遇》(诗集《豹寓言》)中所写:“空山中,偶然遇到的人/我会记下他们的姓名/以平等的视角,问他们/从哪里来,为什么来/去哪里,为什么去/问了什么,答了什么/我会一个字也不删改地记录/还会记录他们的长相/表情、声音、衣着/携带了什么器物……”诗人问山中一个个偶遇的人“你从哪里来,为什么来,去哪里,为什么去。”这些其实就是人类的终极问题,体现的正是作者的一种深邃的人文关怀。
这本书的写作是严谨的。传统印象中,诗人都是浪漫的,而事实上真正的现代诗人都是非常严谨的,他们所写的都是具体、实在之物——“凡能说的都能说清楚”,他们追求用词的精准。雷平阳更追求“严谨”,他痴迷于具体而微小的细节“以其对应已存在的生命、时间、人与自然的关系”。在《临沧记》的写作过程中,对采写对象他必亲见、亲问,对一些场景都要亲自体验,而在遣词作文上更是力求精准,容不得半点的马虎。不仅用笔在写,为了记录的准确性,他还时常拿出相机拍照。而一些重要的场景,他更是拿出随身携带的一台小型摄像机,将其录制成视频,以便后期写作时把采访的对象描述得更为准确。他的采访扎实、观察细致、描述准确、真实可靠,因而他精准的文字具有着直击人心的力量。
雷平阳对采访对象的选择看似随意,实则有他的坚持,他对民间在野的、自然的,以及在历史的深处闪着幽暗微光的事物更感兴趣。他关注的是临沧的人文性、自然山水的野性,如他在诗集《豹寓言》中所说:“如果没有群山、河流、灵异的村寨和有着古老生活习俗的族群作为我写作的摹本,我甚至会觉得写作对我而言是没有意义的。”诗人看似“随意”的事实构象,写出临沧的历史沧桑感和文化厚重感。因而他笔下所呈现的是一个带有雷平阳特质的奇诡、富丽、神秘的临沧。
这本书的写作中作者一直都“在场”。诗人以临沧大地为根基,捕捉这块土地上万物所交织的声音,这种“眼耳鼻舌身意”一直在场的写作具有着唤醒万物的力量。他贴着临沧大地的肌理来写:傣族民间叙事长诗《一百零一朵花》、白雾中的班列山、南本古茶园、临翔石洞寺、拉祜族创世史诗《牡帕密帕》及迁徙史诗《根古》、澜沧江上的昔归渡口、邦东大雪山、旅行家徐霞客、“茶树演化自然博物馆”白莺山、梅子箐、老虎寨、德昂族创世史诗《达古达楞格莱标》、勐库大雪山上的茶祖……这些事物在他笔下实现了“现实根系”与“超验羽翼”的精妙共生。坚实地贴着大地的有温度的写作,使地域性实现了跨越,因它触及到了人类共通的情感,“地域性”也便找到了通往“世界性”的隐秘轨道,最终使临沧超越了地理坐标上的概念,而成为了通向人类精神共性的密码。
这本书为临沧这块土地上普通人的存在作记。书中出现了众多的临沧茶人,没有猎奇,所写都是他们的日常,呈现的是“存在”本身,如作者所言“是让那些沉默的、边缘的、被遮蔽的生命形态得以开显……呈现那些日常性中的尊严、困顿、欢愉与韧性。”即使是短暂采访、仅留有几行文字的人物,作者也能捕捉到他们存在的尊严与人性的光芒。
我之所以将书中的所写物事和人罗列出来,是为了向《临沧记》这本书中所记录的临沧时空褶皱中的“不变之物”及《临沧记》这部著作表示致敬。
某种程度上雷平阳在《临沧记》中所写的人和物事都是超越时空而存在的,它们像是一条河流里品质坚硬的石头,无论河上的泡沫如何涌动,这些石头还是这条河流最基础的载体,是历史长河中的“不变之物”。作者无意在转瞬即逝的“现象”上花心思,反而对这些“不变之物”充满着好奇。如他在书中写沧源岩画时所说:“无论时间的战争波及面有多大,多深,破坏掉的东西有多少,生活中值得纳入画面的事物其实也就那么一点儿,昔在如此,现在也如此,不会有全面的取代和彻底的埋葬,‘不变’之变,变的是外形,不是骨头。”作者在临沧的时空褶皱中所摄取的一个个片段,正具有着这种“不变”的永恒性。
诗人雷平阳对临沧是有感情的。他说:“临沧是澜沧江文明最大的一个摇篮,同时,临沧还是一个有山有水、有丰富多元文化的地方,这些文化很多被现代文明疏远了,现在是让我们转头回去寻找的时候了。在文化上,可以回到山寨去,回到古老的文化上去;在自然里,可以回到桃花源一样的地方去,走到自己的记忆里面。这样的一个地方,在世界上并不多。我们谈所谓的乡愁,其实临沧就是一个巨大的乡愁。”临沧在诗人面前铺开了“一片由时间和文明碎片构成的新的原野”,这让他再次来到了临沧,写下了这本具有“异质之美”的《临沧记》。
深扎泥土的“在场性”与仰望星空的超越性写作,使《临沧记》一书具有了人类学、民俗学、社会学、历史学、地理学、诗学、茶学的多重价值和意义。《临沧记》中作者以独特的视角、敏锐的洞察力、深邃的人文思想及瑰丽的想象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别样的临沧,书中所呈现的一切,对我们自以为很熟悉临沧的人仍有着惊艳之感。如作者所言“在云南茶山中我行走了二十余年,孤旅或求证,茶主题之外,共同演绎的神话与传说、现实与梦境的交替现场、时间的遗迹与事物的复活,我都充满了好奇心,澜沧江的此岸与对岸俨然已经被我当成了前往银河的人间渡口。”而以濒临澜沧江而命名的临沧正是作者“人间渡口”中的重要一站。
这本书是文体的混搭,里面混搭的韵文体诗歌中有民族创世纪史诗、民歌、民谣、词、赋、古今中外的诗歌、作者创作的诗歌等;散文体混搭的有田野调查笔记、访谈录、民间故事、传说、论文、卷首语、史料及文献索引、哲思笔记等,书中各种文体之间转换纯熟、自然、妥帖,显现了作者的博学和对文本超强的掌控能力。
诗人游历临沧两个多月,写下了《临沧记》和《豹寓言》两部关于临沧的书,我以为出版时这两部书是可以做成一函的。散文《临沧记》衍生的诗歌《豹寓言》所显现出的文学价值同样也是无法替代的,诗作为文学的最高形式的原则在这里依然是成立的。某种程度上,《临沧记》倒成了诗集《豹寓言》产生的背景和注释。两部书无疑都已成为书写临沧的好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