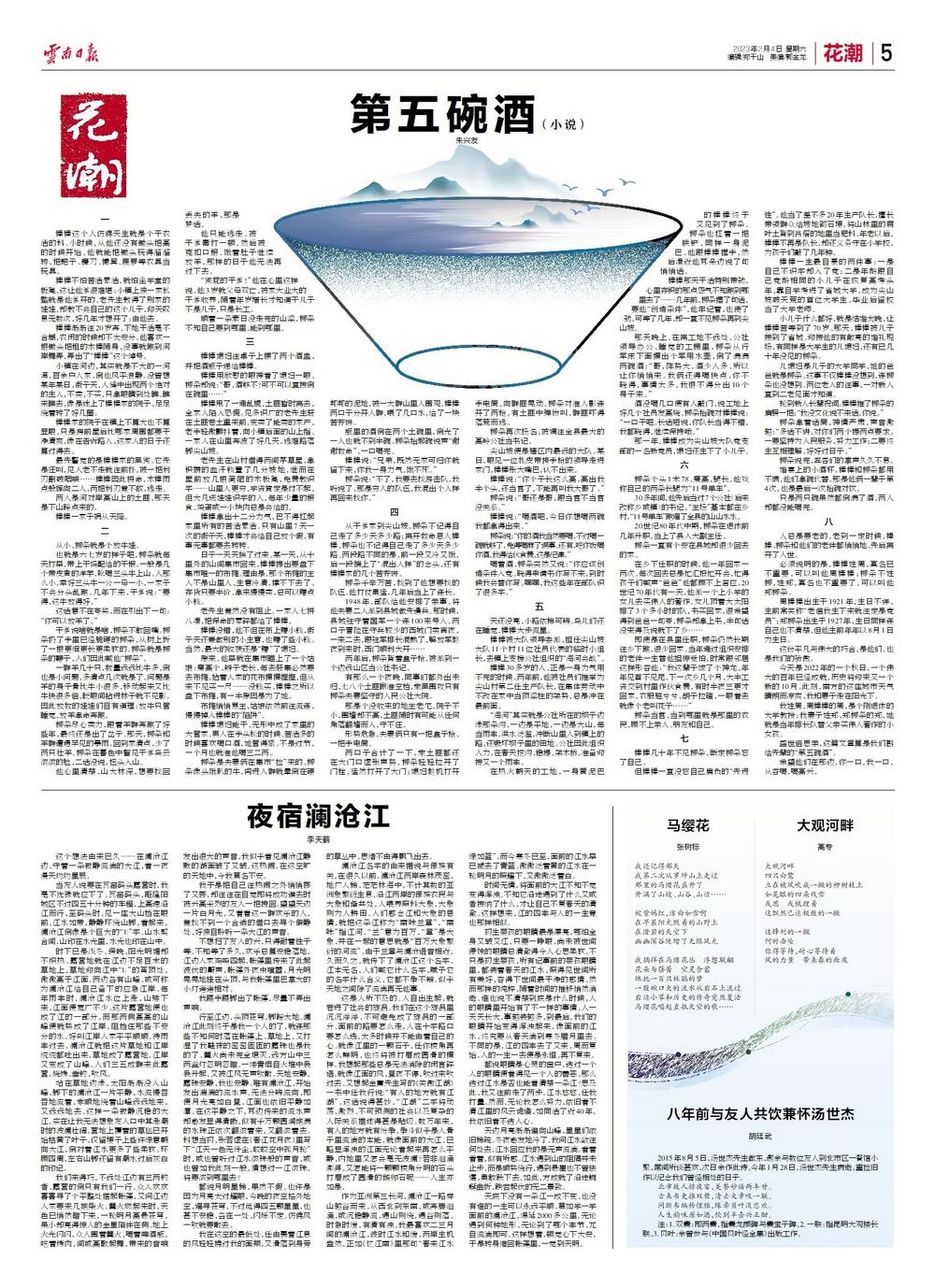朱兴友
一
棒棒这个人仿佛天生就是个干农活的料。小时候,从他还没有锄头把高的时候开始,他就能把锄头玩得溜溜转,把耙子、镰刀、撮箕、篾箩等农具当玩具。
棒棒不怕苦活累活,就怕坐学堂的板凳。这让他爹很难堪:小镇上独一家私塾就是他爹开的。老先生教得了别家的娃娃,却教不会自己的这个儿子,仰天叹息无数次,好几年才想开了:由他去。
棒棒渐渐往20岁奔,下地干活毫不含糊,农闲的时候却不太安分。他喜欢一根锄头把粗的木棒随身,没事就跑到河岸舞弄,弄出了“棒棒”这个绰号。
小镇在河边,其实就是不大的一河湾,百余户人家,倒也风平浪静。没曾想某年某日,街子天,人缝中出现两个绝对的生人,不卖,不买,只拿眼睛到处瞧。瞧来瞧去,像是迷上了棒棒家的院子,足足绕着转了好几圈。
棒棒家的院子在镇上不算大也不算显眼,只是房前屋后比哪家周围都要干净清爽,像在告诉路人,这家人的日子还算过得去。
最先警觉的是棒棒家的黑狗。它先是狂叫,见人老不走就往前扑,被一把利刃割破咽喉……棒棒因此拼命,木棒雨点般挥向二人,两把利刃竟不敌,逃走。
两人是河对岸高山上的土匪,那天是下山踩点来的。
棒棒一家子祸从天降。
二
从小,柳条就是个放牛娃。
也就是六七岁的样子吧,柳条就每天打早,带上干妈配给的干粮,一般是几个带皮煮的洋芋,吆喝三头牛上山。人那么小,幸好三头牛一公一母一小,一家子不会分头乱跑。几年下来,干爹说:“要得,这牛放得好。”
这话意不在夸奖,而在引出下一句:“你可以放羊了。”
干爹说啥就是啥,柳条不敢回嘴。柳条扔了手里已经脆硬的柳条,从树上折了一根更细更长更柔软的。柳条就是柳条的鞭子,人们因此喊他“柳条”。
一群羊几十只,数量远远比牛多,倒也是小问题,多清点几次就是了。问题是羊的身子骨比牛小很多,移动起来又比牛快很多倍,眨眼间钻进林子就不见影。因此放牧的娃娃们自有道理:放牛只管睡觉,放羊拿命奔跑。
柳条尽心卖力,跟着羊群奔跑了好些年,最终还是出了岔子。那天,柳条和羊群遭遇罕见的暴雨。回到家清点,少了两只壮羊。柳条在暮色中瞥见干爹乌云滚滚的脸,二话没说,扭头入山。
他心里清楚,山大林深,想要找回丢失的羊,那是梦话。
他只能逃走。被干爹毒打一顿,然后被克扣口粮、饿着肚子继续放羊,那样的日子他无法再过下去。
“狗屁的干爹!”他在心里这样说。他3岁就父母双亡,被家大业大的干爹收养,随着年岁增长才知道干儿子不是儿子,只是长工。
顺着一条素日没走完的山梁,柳条不知自己要到哪里、能到哪里。
三
棒棒媳妇往桌子上摆了两个酒盅,并把酒瓶子递给棒棒。
棒棒用欣慰的眼神看了媳妇一眼。柳条却说:“哥,酒够不?可不可以直接倒在碗里……”
棒棒甩了一通乱棍,土匪暂时离去,全家人陷入恐慌。见多识广的老先生赶在土匪卷土重来前,变卖了能卖的家产,老手轻微颤抖着,向小镇后面的山上指。一家人在山里奔波了好几天,逃难路落脚尖山坡。
老先生在山村借得两间茅草屋,拿积攒的血汗钱置了几分坡地,继而在屋前放几根简陋的木板凳,免费教识字——山里人更穷,学资肯定是付不起,但大凡送娃娃识字的人,每年少量的粮食、鸡蛋或一小块肉总是会给的。
棒棒拿出十二分力气,巴不得扛起家里所有的苦活累活。只有山里7天一次的街子天,棒棒才会给自己放个假,有事无事都要去转转。
日子一天天挨了过来。某一天,从十里外的山间集市回来,棒棒提出要盘下集市唯一的布摊。理由是,那个布摊的主人不是山里人,生意冷清,撑不下去了,存货只要半价,拿来慢慢卖,总可以赚点小钱。
老先生竟然没有阻止。一家人七拼八凑,把保命的零碎都给了棒棒。
棒棒没错,他不但在布上赚小钱,街子天还兼做别的小生意,也赚了些小钱。当然,最大的收获还是“赚”了媳妇。
原来,他早就在集市瞄上了一个姑娘:瘦高个,辫子老长,每去赶集必然要去布摊,拈着人家的花布摸摸捏捏,但从来不见买一尺——没钱买。棒棒之所以盘下布摊,有一半原因是为了她。
布摊悄悄易主,姑娘依然前往流连,慢慢掉入棒棒的“陷阱”。
棒棒媳妇能干,无形中成了家里的大管家。男人在手头松的时候、苦活多的时候喜欢喝口酒,她管得紧。不是过节,一个月也就准他喝三二两。
柳条是夫妻俩在集市“捡”来的。柳条像头饿趴的牛,闯进人群就晕倒在硬邦邦的泥地,被一大群山里人围观。棒棒两口子分开人群,喂了几口水,给了一块苦荞饼。
瓶里的酒倒在两个土碗里,倒光了一人也就不到半碗。柳条抬起碗说声“谢谢救命”,一口喝完。
棒棒说:“兄弟,既然无家可归你就留下来,你我一身力气,饿不死。”
柳条说:“不了,我要去找游击队,我听说了,那是穷人的队伍,我混出个人样再回来找你。”
四
从干爹家到尖山坡,柳条不记得自己走了多少天多少路;离开救命恩人棒棒,柳条也不记得自己走了多少天多少路。两段路不同的是,前一段又冷又饿,后一段揣上了“混出人样”的念头,还有棒棒家的几个苦荞饼。
柳条千辛万苦,找到了他想要找的队伍。他打仗勇猛,几年后当上了连长。
1948年,部队给他安排了亲事,将他夫妻二人派到县城做先遣兵。那时候,县城驻守着国军一个连100来号人。两口子冒险在守兵较少的西城门卖宵夜,一来二去,跟驻军排长混熟了,解放军趁夜到来时,西门顺利大开……
两年后,柳条背着盒子枪,被派到一个边远山区当公社书记。
有那么一个夜晚,同事们都外出未归,七八个土匪瞅准空档,乘黑围攻只有柳条夫妻坚守的人民公社大院。
那是个没收来的地主老宅,院子不小,围墙却不高,土匪随时有可能从任何角落翻墙而入,守不住。
形势危急,夫妻俩只有一把盒子枪、一把手电筒。
两口子合计了一下,乘土匪都还在大门口虚张声势,柳条轻轻拉开了门栓,猛然打开了大门;媳妇趁机打开手电筒,向群匪晃动。柳条对准人影连开了两枪,有土匪中弹惨叫,群匪吓得落荒而逃。
柳条再次扬名,被调往全县最大的高岭公社当书记。
尖山坡便是辖区内最远的大队。某日,眼见一位扎皮带挎手枪的领导走进家门,棒棒张大嘴巴,认不出来。
棒棒说:“你个子长这么高,高出我半个头,还当官了,不能再叫我大哥了。”
柳条说:“哥还是哥,跟当官不当官没关系。”
棒棒说:“喝酒吧,今日你想喝两碗我都拿得出来。”
柳条说:“你的酒我当然要喝,不过喝一碗就够了,免得喝麻了误事。还有,吃你饭喝你酒,我得给伙食费,这是纪律。”
喝着酒,柳条突然又说:“你应该创造条件入党。晓得申请书你写不来,到时候我会替你写。嘿嘿,我这些年在部队识了很多字。”
五
天还没亮,小路依稀可辨。鸟儿们还在睡觉,棒棒大步流星。
棒棒被大队领导委派,担任尖山坡大队11个村11位社员代表的临时小组长,去镇上支援公社组织的“海河会战”。
棒棒30多岁的人,正是一身力气用不完的时候。两年前,他被社员们推举为尖山村第二任生产队长,在集体劳动中不改在家中当顶梁柱的架势,总是冲在最前面。
“海河”其实就是公社所在的坝子边缘那条沟,一边是平地,一边是大山,每当雨季,洪水泛滥,冲断山里人到镇上的路,还毁坏坝子里的田地。公社因此组织人力,在春天挖沟、稳堤、架木桥,准备迎接又一个雨季。
在热火朝天的工地,一身黄泥巴的棒棒终于又见到了柳条。柳条也扛着一把铁铲,同样一身泥巴。他跟棒棒握手,然后凑近他耳朵边说了句悄悄话。
棒棒那天干活特别带劲,心里存积的那点怨气不知跑到哪里去了——几年前,柳条撂了句话,要他“创造条件”,他牢记着,也使了劲,可等了几年,却一直不见柳条再到尖山坡。
那天晚上,在离工地不远处,公社领导办公、睡觉的工棚里,柳条从行军床下面摸出个军用水壶,倒了满满两碗酒:“哥,阵势大,酒少人多,所以让你悄悄来。我俩还得喝快点,你不晓得,事情太多,我恨不得分出10个身子来。”
酒没喝几口便有人敲门,说工地上好几个社员发高烧。柳条抬碗对棒棒说:“一口干吧。长话短说,你队长当得不错,我都晓得,继续保持哦。”
那一年,棒棒成为尖山坡大队党支部的一名新党员,媳妇还生下了小儿子。
六
柳条个头1米78,瘦高,腿长。他戏称自己的两条长腿为“11号单车”。
30多年间,他先后当过7个公社(后来改称乡或镇)的书记,“主场”基本都在乡村,“11号单车”跑遍了全县的山山水水。
20世纪80年代中期,柳条在退休前几年升职,当上了县人大副主任。
柳条一直有个安在县城却很少回去的家。
在乡下任职的时候,他一年回家一两次。每次回去总是忙汇报忙开会,忙得孩子们喊声“爸爸”他都顾不上答应。20世纪70年代有一天,他派一个上小学的女儿去买伟人的著作。女儿顶着大太阳排了3个多小时的队,书买回家,很希望得到爸爸一句夸,柳条却拿上书,半句话没来得及说就下了乡……
即使是在县里任职,柳条仍然长期往乡下跑,很少回家。当年通过组织安排的老伴一生替他担惊受怕,时常跟邻居这样形容他:“我这辈子嫁了个神龙,年年见首不见尾,下一次乡几个月,大半工资交到村里作伙食费,有时半夜三更才回家,衣服脏兮兮,胡子拉碴,一眼看去就像个老叫花子……”
柳条当官,当到哪里就是那里的农民,顾不上亲人、朋友和自己。
七
棒棒几十年不见柳条,断定柳条忘了自己。
但棒棒一直没忘自己肩负的“先进性”。他当了差不多20年生产队长,擅长带领群众给坡地砌石埂,将山林里的腐叶土背到贫瘠的地里当肥料。年老以后,棒棒不再是队长,却还义务守在小学校,为孩子们敲了几年钟。
棒棒一生最自豪的两件事:一是自己不识字却入了党;二是年龄跟自己党龄相同的小儿子在恢复高考头年,靠自学考进了省城大学,成为尖山坡破天荒的首位大学生,毕业后留校当了大学老师。
小儿子什么都好,就是结婚太晚,让棒棒苦等到了70岁。那天,棒棒被儿子接到了省城。迎接他的有敞亮的婚礼现场,有同样是大学生的儿媳妇,还有已几十年没见的柳条。
儿媳妇是儿子的大学同学,她的爸爸就是柳条。这事不仅棒棒没想到,连柳条也没想到。两位老人的往事,一对新人直到二老见面才知道。
轮到新人长辈祝词。棒棒推了柳条的肩膀一把:“我没文化说不来话,你说。”
柳条拿着话筒,神情严肃,声音激越:“多话不讲,对你们两个提两点要求,一要坚持为人民服务,努力工作;二要终生互相理解,好好过日子。”
柳条说完,宾客们的掌声久久不息。
婚宴上的小酒杯,棒棒和柳条都用不惯,他们拿碗代替。那是他俩一辈子第4次,也是最后一次抬碗对饮。
只是两只碗虽然都倒满了酒,两人却都没能喝完。
八
人总是要老的,老到一定时候,棒棒、柳条和他们的老伴都悄悄地、先后离开了人世。
必须说明的是,棒棒姓周,真名已不重要,可以叫他周棒棒;柳条不姓柳,姓郑,真名也不重要了,可以叫他郑柳条。
周棒棒出生于1921年,生日不详,生前常笑称“老倌我生下来就注定是党员”;郑柳条出生于1927年,生日同样连自己也不清楚,但他生前年年以8月1日为生日。
这份平凡与伟大的巧合,是他们、也是我们的骄傲。
今天是2022年的一个秋日,一个伟大的百年已经成就,历史将迎来又一个新的10月。此刻,南方的这座城市天气晴朗而凉爽,我和妻子走在阳光下。
我姓周,周棒棒的周,是个刚退休的大学教授;我妻子姓郑,郑柳条的郑,她就是当年排长队替父亲买伟人著作的小女孩。
盛世倍思亲,这篇文章算是我们斟给先辈的“第五碗酒”。
希望他们在那边,你一口,我一口,从容喝,喝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