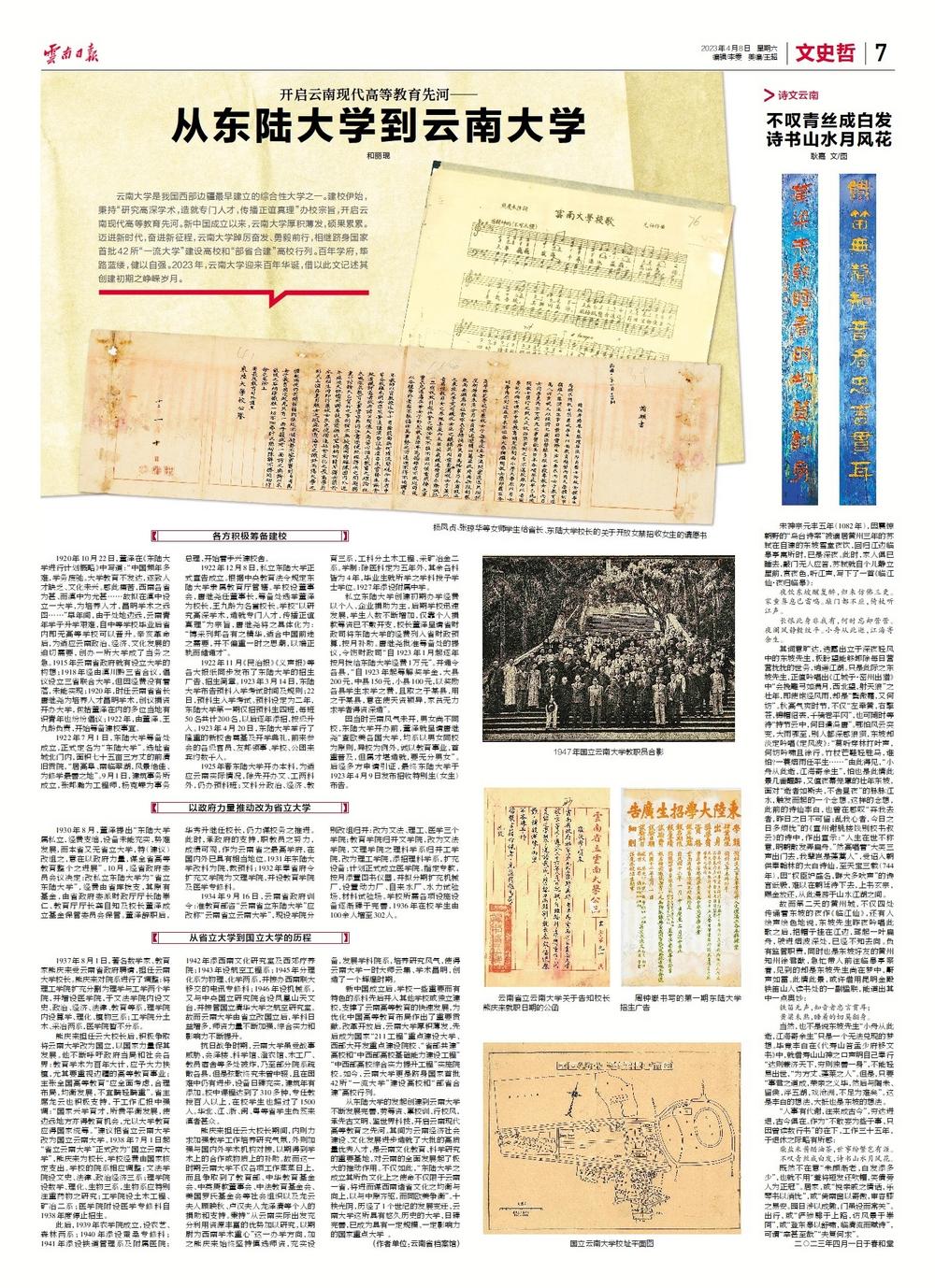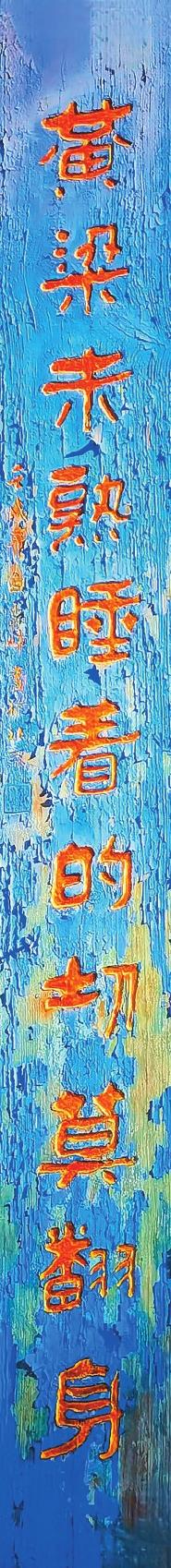耿嘉 文/图
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年),因震惊朝野的“乌台诗案”被谪居黄州三年的苏轼在自建的东坡雪堂夜饮,回归江边临皋亭寓所时,已是深夜。此时,家人俱已睡去,敲门无人应答,苏轼就自个儿静立屋前,赏夜色,听江声,写下了一首《临江仙·夜归临皋》: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其词意旷达,透露出立于深夜轻风中的东坡先生,极盼望能够卸除每日营营扰扰的世务,逍遥江湖。只是此际之东坡先生,正值吟唱出《江城子·密州出猎》中“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之壮年,即使饱经风雨,却是“鬓微霜,又何妨”。秋高气爽时节,不仅“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也可随时等待“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哪怕风云突变,大雨骤至,别人都深感狼狈,东坡却淡定吟唱《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由此得见,“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怕也是此情此景几番醒醉,又值夜幕笼罩的壮年东坡,面对“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脉脉江水,触发而起的一个念想。这样的念想,此前的诗仙李白,也曾在感叹“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的《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的诗中,作出宣示:“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然高唱着“大笑三声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受诏入朝供奉翰林的太白诗仙,至天宝三载(744年),因“权臣妒盛名,群犬多吠声”的谗言诋毁,难以在朝廷待下去,上书玄宗,赐金放还,从此漫游于山水江湖之间。
故而第二天的黄州城,不仅四处传诵着东坡的夜作《临江仙》,还有人绘声绘色地说,东坡先生昨夜吟唱此歌之后,把帽子挂在江边,驾起一叶扁舟,驶进烟波深处,已经不知去向。负有监管职责,同时也是东坡好友的黄州知州徐君猷,急忙带人前往临皋亭察看,见到的却是东坡先生尚在梦中,鼾声如雷。此情此景,或许借用昆明金殿铁笛山人读书处的一副楹联,能道出其中一点奥妙:
铁笛无声,知音者忠言贯耳;
黄粱未熟,睡着的切莫翻身。
当然,也不是说东坡先生“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只是一个无法兑现的梦想。毕竟李白在《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中,就借寿山山神之口声明自己奉行“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一身”,不能轻易出世,“为方丈、蓬莱之人”。但是,只要“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然后与陶朱、留侯,浮五湖,戏沧洲,不足为难矣”。这是李白的想法,大抵也是东坡的想法。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穷达进退,古今俱在。作为“不敢妄为些子事,只因曾读数行书”的在下,工作三十五年,于退休之际略有所感:
柴盐米酱醋油茶,世事纷繁岂有涯。
不叹青丝成白发,诗书山水月风花。
既然不在意“朱颜渐老,白发添多少”,也就不用“羞将短发还吹帽,笑倩旁人为正冠”。居家,或“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或“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出行,或“俨骖騑于上路,访风景于崇阿”,或“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可谓“幸甚至哉”“夫复何求”。
二〇二三年四月一日于春和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