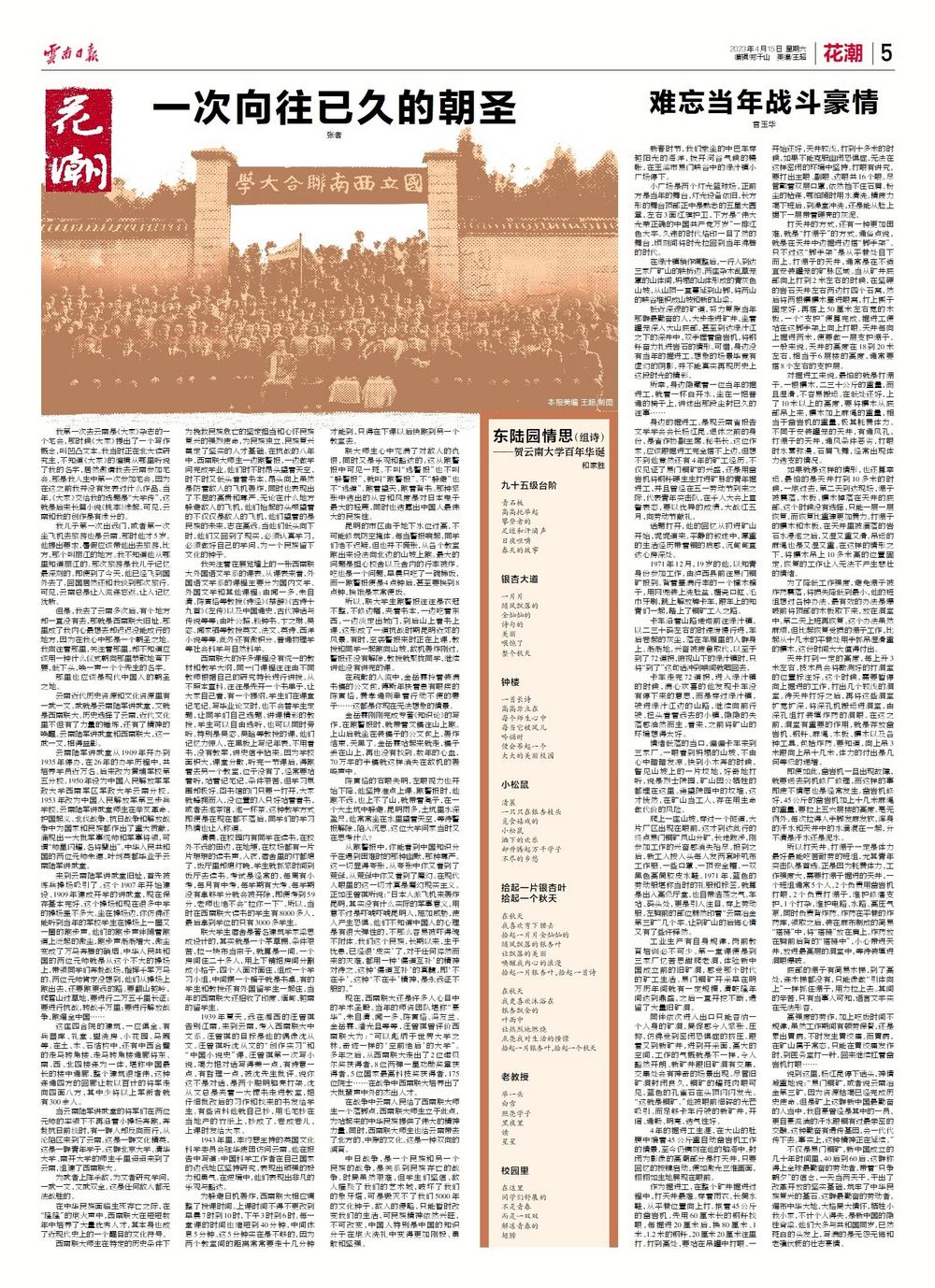官玉华
新春时节,我们乘坐的中巴车穿越阳光的海洋,拨开河谷气候的幔帐,在玉溪市易门峡谷中的绿汁镇小广场停下。
小广场是两个灯光篮球场,正前方是当年的舞台,灯光设备依旧,长方形的舞台顶部正中是熟悉的五星大圆章,左右3面红旗护卫,下方是“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一排红色大字。久违的时代烙印一目了然的舞台,顷刻间将时光拉回到当年沸腾的时代。
在绿汁镇稍作调整后,一行人到达三家厂矿山的铁桥边。两座杂木乱草笼罩的山体间,坍塌的山体形成的青灰色山坡,从山顶一直蔓延到山脚,将两山的峡谷堆积成山坡和新的山梁。
抵近深邃的矿道,努力复原当年那群最勤奋的人,大步走进矿井,坐着罐笼深入大山底部,甚至到达绿汁江之下的深井中,双手握着凿岩机,将钢钎奋力扎进岩石的情形。可惜,身边没有当年的掘进工,想象的场景毕竟有虚幻的阴影,并不能真实再现历史上这段时光的精彩。
所幸,身边隐藏着一位当年的掘进工,就着一杯白开水,坐在一把普通的椅子上,讲述出那段尘封已久的往事……
身边的掘进工,是现云南省报告文学学会会长杨红昆。退休之前的身份,是省作协副主席、秘书长。这位作家,应该跟掘进工完全搭不上边,但想不到他竟然还有4年的矿工经历。不仅见证了易门铜矿的兴盛,还是用凿岩机将钢钎硬生生打进矿脉的青年掘进工,并且曾经在五一劳动节到来之际,代表青年突击队,在千人大会上宣誓表态,要以优异的成绩,大战红五月,向劳动节献礼。
话题打开,他的回忆从初进矿山开始,娓娓道来。平静的叙述中,厚重的生活经历带着铜的质感,沉甸甸直达心房深处。
1971年12月,19岁的他,以知青身份参加工作,由泸西县前往易门铜矿报到。背着塞满行李的一个樟木箱子,用网兜装上洗脸盆、搪瓷口缸、毛巾牙刷,跳上解放牌卡车,跟车上的知青们一起,踏上了铜矿工人之路。
卡车沿着山路逶迤前往绿汁镇,以二三十码左右的时速缓慢行进,车后卷起的灰尘,落在车厢里的人群身上。渐渐地,兴奋被疲惫取代,以至于到了72道拐,俯视山下的绿汁镇时,只将“到了”这句话冲到喉间就咽回去。
卡车走完72道拐,进入绿汁镇的时候,满心欢喜的他发现卡车没有停下来的意思,而是穿过绿汁镇,驶进绿汁江边的山路,继续向前行驶。扭头看着远去的小镇,隐隐的失落感油然而生。看来,之前将矿山的环境想得太好。
情绪低落的当口,偏偏卡车来到三家厂。一眼看到坍塌的山坡,不由心中暗暗发凉。快到小木奔的时候,瞥见山坡上的一片坟地,好奇地打听,说是烈士陵园,矿山因公牺牲的都埋在这里。遥望陵园中的坟堆,这才恍然,在矿山当工人,存在用生命做代价的风险。
爬上一座山坡,穿过一个隧道,大片厂区出现在眼前,这才到达此行的终点易门铜矿凤山分矿。长途跋涉,刚参加工作的兴奋感消失殆尽。报到之后,新工人按人头每人发两套咔叽布工作服、一些口罩、一顶安全帽、一双黑色高筒胶皮水鞋。1971年,蓝色的劳动服堪称当时的礼服和标签,就算是出入高级厅堂,也自带浩荡之气。车站、码头处,更是引人注目。穿上劳动服,左胸前的部位赫然印着“云南冶金第三矿”几个字。让到矿山的后悔心情又有了些许释然。
工业生产有自身规律,岗前教育培训必不可少。第一堂课便是到三家厂忆苦思甜爬老洞,体验新中国成立前的旧矿洞,感受那个时代的矿工生活。易门铜矿开采早在明万历年间就有一定规模,清乾隆年间达到鼎盛,之后一直开挖不断,遗留了大量旧矿洞。
同伴依次进入出口只能容纳一个人身的矿洞,局促感令人紧张、压抑,仿佛受到密闭恐惧症的挤压。跟着又到新矿井,进到开采面,高大的空间,工作的气概就是不一样,令人豁然开朗。新矿井跟旧矿洞有交集,交集处会有神奇的场景出现。尽管旧矿洞封闭良久,铜矿的耀斑肉眼可见,蓝色的孔雀石在头顶闪闪发光。“这就是铜矿。”他被眼前细碎的光芒吸引。而足够卡车行驶的新矿井,开阔、通畅、明亮、透气性好。
4年的掘进工生涯,在大山的肚腹中端着45公斤重自动凿岩机工作的情景,至今仍镌刻在他的脑海中。封闭为影像的高潮部分是打天井,只要回忆的按键启动,便如激光三维画面,栩栩如生地展现在眼前。
作为掘进工,在整个矿井掘进过程中,打天井最难。穿着雨衣、长筒水鞋,从平巷位置向上打。抱着45公斤的凿岩机,先用60厘米长的钢钎找眼,每掘进20厘米后,换80厘米、1米、1.2米的钢钎,20厘米20厘米往里打。打到高处,要站在吊罐中打眼。一开始还好,天井较浅,打到十多米的时候,如果不能克服幽闭恐惧症,无法在这样密闭的环境中坚持。打眼有讲究,要打出主眼、副眼、边眼共16个眼。尽管戴着双层口罩,依然挡不住石屑、粉尘的粘连,哪怕随时用水清洗。精疲力竭下班后,到澡堂冲洗,还是能从脸上揭下一层带着硬壳的灰泥。
打天井的方式,还有一种更加困难,就是“打绷子”的方式。通俗点说,就是在天井中边掘进边搭“脚手架”。只不过这“脚手架”是从平巷处自下而上。打绷子的天井,通常是在不适宜安装罐笼的矿脉区域。当从矿井底部向上打到2米左右的时候,在坚硬的岩石天井左右两边打四个石窝,然后将两根镶欀木塞进眼窝,打上楔子固定好,再搭上50厘米左右宽的木板,一个“支护”便算完成。掘进工便站在这脚手架上向上打眼。天井每向上掘进两米,便要做一层支护绷子。一般来说,天井的高度在18到20米左右,相当于6层楼的高度,通常要搭8个左右的支护层。
对掘进工来说,最怕的就是打绷子。一根欀木,二三十公斤的重量,而且湿滑,不容易搬运。在低处还好,上了10米以上的高度,要将欀木从底部吊上来,欀木加上麻绳的重量,相当于凿岩机的重量,极其耗费体力。不同于安装罐笼的天井,有通风孔,打绷子的天井,通风条件恶劣,打眼时水雾弥漫,石屑飞舞,经常出现体力透支的情况。
如果就是这样的情形,也还算幸运。最怕的是天井打到10多米的时候,一炮过去,第二天到达现场,绷子被震落,木板、欀木掉落在天井的底部。这个时候没有选择,只能一层一层恢复。而恢复比重建更加费力。打绷子的欀木和木板,在天井里被滴落的岩石水浸泡之后,又湿又重又滑。吊运的麻绳也是又湿又重。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将欀木吊上10多米高的位置固定,恢复的工作让人无法不产生悲壮的情绪。
为了降低工作强度,避免绷子被炸药震落,将损失降低到最小,他的班组想过各种办法。最有效的办法是爆破前将顶部的木板取下来,放在洞室中。第二天上班再恢复。这个办法虽然麻烦,但比起恢复受损的绷子工作,比起从十几米的平巷处用手抓吊湿滑重的欀木,这份时间大大值得付出。
天井打到一定的高度,每上升3米左右,技术员会将勘测好的打洞室的位置标注好。这个时候,需要暂停向上掘进的工作,打出几个较浅的洞室。待天井打好之后,再将这些洞室扩宽扩深,将深孔机搬运进洞室,由深孔组打装填炸药的洞眼。在这之前,洞室有重要的作用,就是存放凿岩机、钢钎、麻绳、木板、欀木以及各种工具,包括炸药。要知道,向上吊3米跟向上吊十几米,体力的付出是几何等级的递增。
即便如此,凿岩机一旦出现故障,就要送去到机修厂修理,而这样的事即使不情愿也是经常发生。凿岩机修好,45公斤的凿岩机加上十几米麻绳的重量,要拉上五六层楼的高度。毫无例外,每次拉得人手脚发麻发软,浑身的汗水和天井中的水滴混在一起,分不清是汗水还是泥水。
所以打天井、打绷子一定是体力最好最能吃苦耐劳的班组,尤其青年突击队是首选。正是因为耗费体力,工作强度大,需要打绷子掘进的天井,一个班组通常5个人。2个负责用凿岩机打眼,2个负责打绷子,维护修缮支护,1个打杂,维护电路、水路、高压气泵,同时负责背炸药。炸药在平巷的炸药库,领取之后,装在麻布制成的简易“褡裢”中,将“褡裢”放在肩上,炸药放在胸前后背的“褡裢中”,小心带进天井,放进最高层的洞室中,等待装填进洞眼爆破。
底部的绷子有简易木梯,到了高处,连木梯都没有,只能像做“引体向上”一样抓住绷子,用力拉上去。其间的辛苦,只有当事人可知,语言文字实在无法形容。
高强度的劳作,加上吃饭时间不规律,虽然工作期间有顿劳保餐,还是累出胃病,不时发生胃绞痛。而胃病,在矿山属于常态,只能在胃绞痛发作时,到医务室打一针,回来继续扛着凿岩机打眼……
说到这里,杨红昆停下话头,神情凝重地说:“易门铜矿,或者说云南冶金第三矿,因为资源枯竭已经完成历史使命。但是矿上这群新中国最勤奋的人当中,我自豪曾经是其中的一员,更自豪流淌的汗水跟铜有过最亲密的交融。这种勤奋有遗传基因,会一代代传下去。事实上,这种精神正在延续。”
不仅是易门铜矿,新中国成立的几十年时间里,40后到60后,这群称得上全球最勤奋的劳动者,带着“只争朝夕”的信念,一天当两天干,干出了改革开放的坚实基础,筑牢了中华民族复兴的基石。这群最勤奋的劳动者,遍布中华大地,大格局大情怀,牺牲小我小家,不计个人得失,是新中国的隐性脊梁。他们大多与共和国同岁,已然斑白的头发上,写满的是无怨无悔和老骥伏枥的壮志豪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