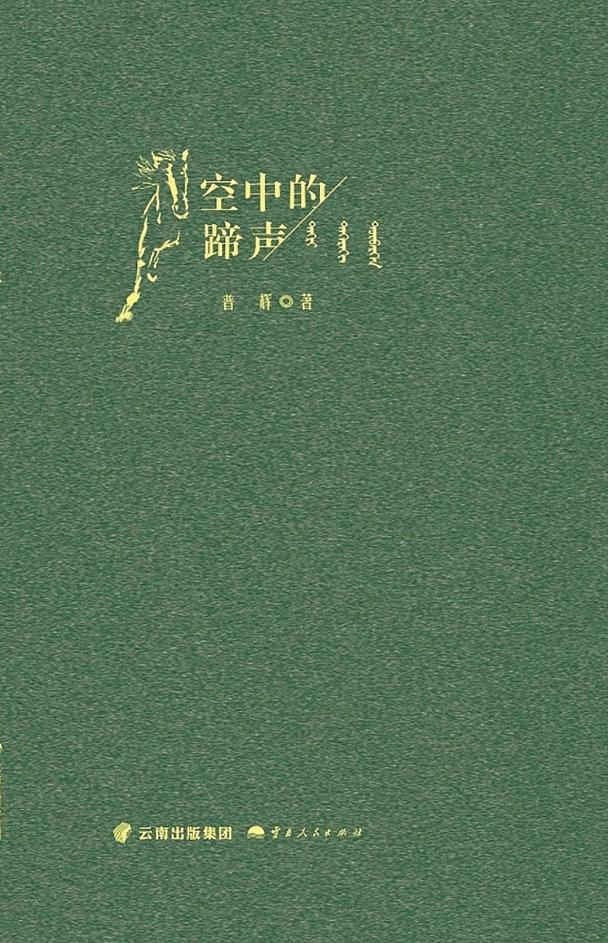付冯选
在云南,提及蒙古族,自然会让人想到玉溪市通海县兴蒙蒙古族乡。兴蒙乡是云南唯一的蒙古族乡,这里传承着那达慕、鲁班节、忆祖节等多种传统节日和民族文化。“南陲开边苦,滇域埋忠骨,驰骋七百载,北眷草原土。”兴蒙乡的蒙古族,是当年随忽必烈的军队征战云南时镇守河西镇、驻守杞麓山的蒙古士兵留下的后裔,他们的文化传承至今已有700多年的历史。
追本溯源,中华优秀文化是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源泉,保护和传承民族文化,讲好各民族文化的共同性,有助于增进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归属感、安顿感,增强民族凝聚力、向心力和亲和力。
诗人普辉是蒙古族,以书法名世,古典文学修养自然不薄,然而云南人民出版社2022年4月出版发行的《空中的蹄声》却是一部诗集。诗集分为5章,每章有前奏、尾音,各声部交响。诗人一开始便点出:“谛听马蹄声”是为了“寻找踪迹”,以便将“七百多年的故土/带回,洒在兴蒙”(《序诗》)。
首先,我们见到的是一种姿态,回溯的姿态。“向西,一路向西//沿忽必烈当年的行军路线,逆行”(《去滇西》),过金沙江,“七百多年前的马蹄声/一路回响”,但“找到的词语/能否完成对历史的叙述”(《去金沙江》)?此刻,诗人是犹疑的,面对历史的黄沙,寻找记忆难如凌空蹈虚,只有诗集完成,才能验证。从元世祖开始,南下蒙古人行军的陈迹尚在(《革囊渡》),如马蹄声在空中回响,形成对诗人的召唤和挑战。“听”作为一种姿态,是为追随祖先的路,是为慎终追远,找到并确证自己。虽然,诗人心怀故乡,但诗人已然远离草原,这是现实,“即使我/胸膛热血奔涌,在江边/不停地呼喊,也搅不动一江春水”,而“追寻蒙古”的目的“也只是在祖先经过时/遗留的革囊渡,找到出处/像拥有身份证”(《饮江水》)。无疑,这本诗集的目的正在于确证诗人在其族群中的身份。正是这样的身份焦虑让诗人踏上寻根之旅,并以诗歌的方式为我们重构了一个精神家园。
止戈为武,元世祖忽必烈即是如此,“那一纸‘止杀令’,让整个世界/复归于平静,免于刀枪剑戟”(《玉龙雪山》),“如果让一个地方血流成河/那我们的血也会流成河”(《地涌金莲》),然而追溯的脚步必须融入其中才能真正做到谛听,“看来我得先沉入江底/跟鱼群一起洄游”(《太子关》)。倾听即是对话,南下的蒙古祖先对众生的敬畏,才是其在云南得以落脚的根本(《玉峰寺》)。而在《遥望巨甸》一诗中,诗人道出了自身的理解,也许对于追寻而言,答案其实是不必要的,更为重要的是“融入”其中,并心怀感恩。合适的距离是接近、抵达的条件,接下来,诗人沿着“蛛丝马迹”(龙首关、五华楼、苍山洗马潭、平云南碑、曲陀关)向“未知的世界”一路探寻。途经松华坝、昆明文庙、测影所、惠民药局、帅府桃林、忠爱坊,诗人忆起了郭守敬、马可·波罗、阿盖公主,尤其赛典赤·赡思丁。当然,怀古不是为了文化返祖,而是为慎终追远,进而确证自我,最终更为深沉地爱这片土地——云南。通过赛典赤·赡思丁田间问租一事的书写,诗人明确了人民情怀才是蒙古祖先留给兴蒙的真正遗产(《田间问租》)。
待历史的尘埃终于落定,“马蹄声渐渐消失/船舷的桨橹声常常响起/只有长调和马头琴/悠然回味”(《飘落的云》)。蒙古人的生活方式也开始了从游牧到打鱼的转变,“哪里有牛羊,长调变成短笛/长袍割成短袄,弓箭不能挽了/改作梭子,织渔网”(《月冷陀关》),“带着对草原的记忆/再也没有回到草原”(《仙人桥》),因此,“失去了草原和骏马”“常年漂泊在杞麓湖/捕鱼捞虾”(《渔夫堆》),自此开启了“不堪回首又抹不掉的日子”(《独自倾听》),也就有了后面诗人对谋生手艺的礼赞(《迷失的春天》)。很显然,诗人苦苦追寻的蒙古并非现成之物,而是通过意象(旋律)一次次叩醒记忆,连缀、建构起来的兴蒙历史图像。随着交往交流交融的进一步深化,各民族都融进了中华民族大家庭。那么,诗人心中的兴蒙到底在哪里呢?可以说,像时光一样,无处不在,“藏在大地深处,藏在/隐秘的山林,藏在虚拟的传说/藏在服饰,藏在一个个符号”,如仙人桥、马刨井、旃班、接柴、姑娘龙、弦歌洞、喀卓语和三叠水等,“与兴蒙有关的传说、习俗或事物”之中(《时光藏在……》)。
虽然离开北方,但“他们并没有忘记来时的路/给自己起了带着烙印的名字:兴蒙”(《兴蒙、兴蒙》)。诗人通过对小海塘、百花巷、艾思奇、白沙凹、那达慕、赵昆、顶碗舞、滇南、凤凰山等意象的梳理,追寻的焦虑似乎终于得到缓解,生活也开始步入新的阶段,甚至变甜,“远离故土,失去了草原/和草原上奔驰的骏马/就当转了个身,在大海中/破浪前行,即使用锄头/也要挖出一片碧蓝的天地”(《在甜瓜节》)。与此同时,诗人与兴蒙人的情感也汇聚到了对祖国情感的河流之中,只剩下一个“尾音”——“我的心其实很小/只装得下中国两个字”。至此,随着作者自我确证的完成,兴蒙的诗意叙事也藉此得以完成。
另外,值得一说的是诗人的语言,雅正、硬朗,绝不拖沓、繁复。譬如,“在杞麓湖边,头顶柳条/寄身芦苇”(《饮江水》);“他借来/满天星斗,点亮殿堂”(《昆明文庙》);“树木、荒草、荆棘……疯狂地占据/每一处土地,比人类更疯狂/暗示谁是大地的主人,还暗示/随遇而生的谋略”(《立道劝农》),等等。就整首诗而言,《埜喇》《迷失的春天》尤为精彩。
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将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坚实的精神和文化基础,而诗人个人对历史文化的诗意叙述无疑是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参与方式。普辉的这部诗集,仿佛一曲大型的音乐史诗,一首首小诗就像其中的一段段旋律或剖面,众声合奏或构筑出一种不仅属于诗人个人的兴蒙诗意叙事,也可以看成是对寻根精神的一种个体化的呼应。最后,在完成历史叙述的同时,诗人也终于完成了自我确证,获得了一种文化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