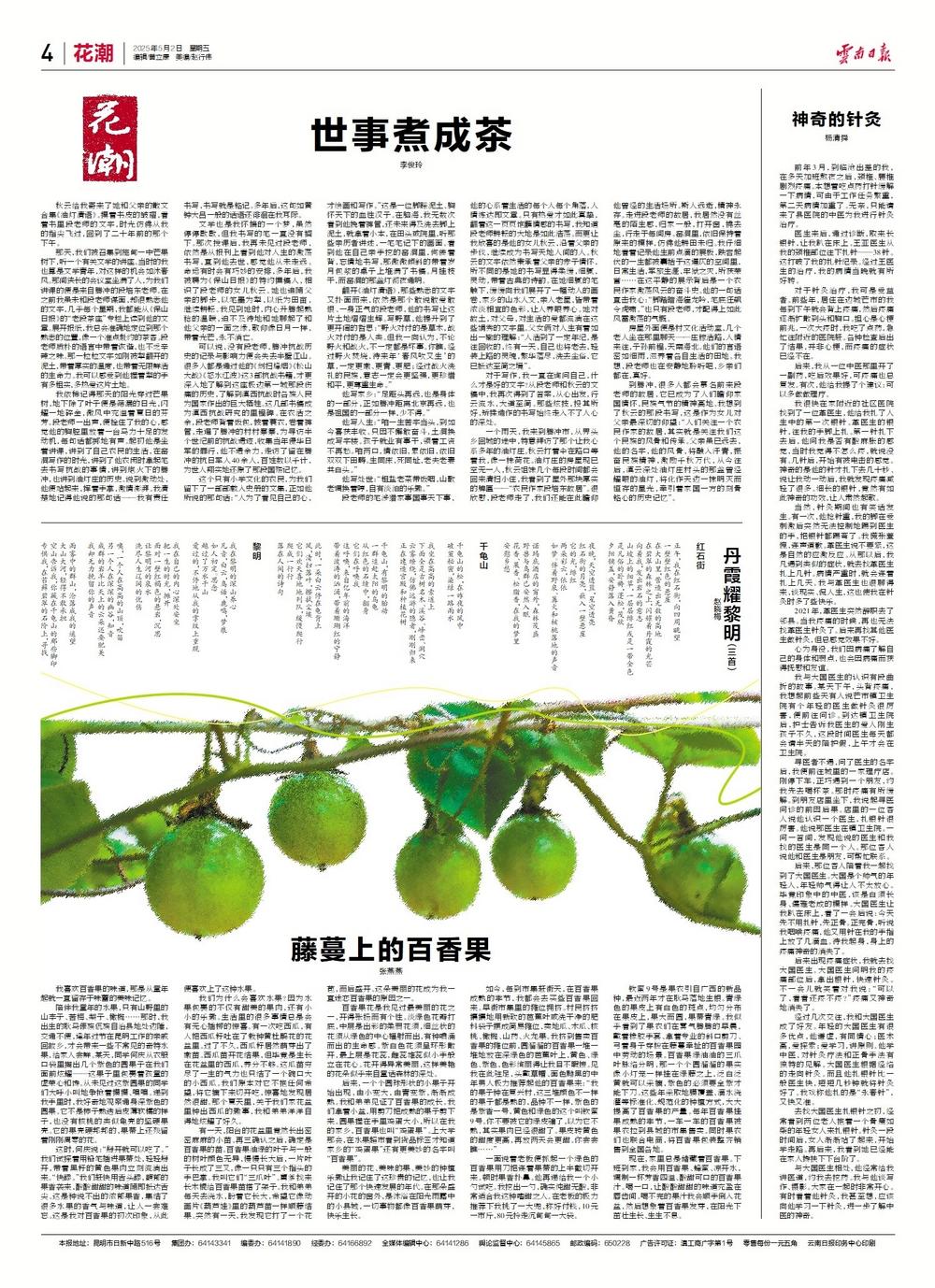李俊玲
秋云给我寄来了她和父亲的散文合集《油灯清语》。摸着书皮的皱褶,看着书里段老师的文字,时光仿佛从我的指尖飞过,回到了二十年前的那个下午。
那天,我们被召集到施甸一中芒果树下,听一个有关文学的讲座。当时的我也算是文学青年,对这样的机会如沐春风。那间狭长的会议室坐满了人,为我们讲课的便是来自腾冲的段培东老师。在之前我虽未和段老师谋面,却很熟悉他的文字,几乎每个星期,我都能从《保山日报》的“老段茶座”专栏上读到他的文章。展开报纸,我总会准确地定位到那个熟悉的位置,像一个准点赴约的茶客。段老师质朴的语言中带着诙谐,也不乏辛辣之味。那一粒粒文字如刚被犁翻开的泥土,带着厚实的温度,也带着无限鲜活的生命力。我可以感受到他握着犁的手有多粗实,多热爱这片土地。
我依稀记得那天的阳光穿过芒果树,地下除了叶子便是筛漏的日光,闪耀一地碎金,微风中充溢着夏日的芬芳。段老师一出声,便拴住了我的心,感觉他的胸腔里放着一台马力十足的发动机,每句话都掷地有声。起初他是坐着讲课,讲到了自己农民的生活,在窑洞写作的时光,讲到了他农闲时拿起笔去书写抗战的事情,讲到炮火下的腾冲,也讲到油灯庄的历史。说到激动处,他便站起来,挥着手掌,激情澎湃。我清楚地记得他说的那句话——我有责任书写,书写就是铭记。多年后,这句如黄钟大吕一般的话语还徘徊在我耳际。
文学也是我怀揣的一个梦,虽然停停歇歇,但我书写的笔一直没有搁下。那次授课后,我再未见过段老师,依然是从报刊上看到他对人生的激荡书写,直到他去世,感觉他从未走远。命运有时会有巧妙的安排,多年后,我被聘为《保山日报》的特约撰稿人,相识了段老师的女儿秋云。她也追随父亲的脚步,以笔墨为犁,以纸为田亩,继续耕耘。我见到她时,内心升腾起熟稔的温暖,迫不及待地和她聊起了和他父亲的一面之缘,敬仰像日月一样,带着光芒,永不消亡。
可以说,没有段老师,腾冲抗战历史的记录与影响力便会失去半壁江山。很多人都是通过他的《剑扫烽烟》《松山大战》《怒水红波》这3部抗战书籍,才更深入地了解到这座极边第一城那段伤痛的历史,了解到滇西抗战时各族人民为国家作出的巨大牺牲。这几部书稿成为滇西抗战研究的里程碑。在农活之余,段老师背着饭包,披着蓑衣,卷着裤管,走遍了腾冲的村村寨寨,为寻访半个世纪前的抗战遗迹,收集当年侵华日军的罪行,他不遗余力,走访了留在腾冲的抗日军人40余人,百姓数以千计,为世人翔实地还原了那段国殇记忆。
这个只有小学文化的农民,为我们留下了一部部载入史册的文集,正如他所说的那句话:“人为了看见自己的心,才绘画和写作。”这是一位脚踩泥土、胸怀天下的血性汉子。在脑海,我无数次看到他挽着裤管,还未来得及洗去脚上泥土,就拿着小本,在田头或院里,听那些亲历者讲述,一笔笔记下的画面。看到他在自己亲手挖的窑洞里,佝偻着背,忘情地书写,那微微倾斜的带着岁月包浆的桌子上堆满了书稿。月挂枝干,而窑洞的那盏灯彻夜通明。
翻开《油灯清语》,那些熟悉的文字又扑面而来,依然是那个敢说敢爱敢恨、一身正气的段老师,他的书写让这片土地熠熠生辉。写野草,他提升到了更开阔的哲思:“野火对付的是草木,战火对付的是人类。但我一向认为,不论野火和战火,不一定都是坏事。你瞧,经过野火焚烧,待来年‘春风吹又生’的草,一定更嫩、更青、更肥;经过战火洗礼的民族,意志一定会更坚强,更珍惜和平,更尊重生命。”
他写家乡:“足距头再远,也是身体的一部分,正如腾冲距离北京再远,也是祖国的一部分一样,少不得。”
他写人生:“咱一生苦字当头,到如今喜获丰收。只因不懈敢奋斗,土洞换成写字楼。孩子就业有事干,领着工资不再愁。咱两口,情依旧,累依旧,依旧双双下田畴。生同床,死同址,老夫老妻共白头。”
他写处世:“粗盐老菜带饭咽,山歌老调换着哼,自有淡泊的乐趣。”
段老师的笔涉猎家事国事天下事,他的心系着生活的每个人每个角落,人情练达即文章。只有热爱才如此真挚,翻着这一页页饱蘸情感的书写,我知道段老师耕耘的大地是如此浩荡。而更让我欣喜的是他的女儿秋云,沿着父亲的步伐,继续成为书写天地人间的人。秋云的文字依然秉承着父亲的赤子情怀,所不同的是她的书写显得柔缓,细腻,灵动,带着古典的诗韵。在她细腻的笔触下,缓缓向我们展开了一幅动人的画卷,家乡的山水人文,亲人老屋,皆带着浓淡相宜的色彩,让人养眼养心。她对故土,对父母,对生活的爱都流淌在这些娟秀的文字里。父女俩对人生有着如出一辙的理解:“人活到了一定年纪,是往回收的,终有一天,自己也将老去,轻装上路的灵魂,繁华落尽,洗去尘俗,它已抵达至简之境”。
对于写作,我一直在询问自己,什么才是好的文字?从段老师和秋云的文稿中,我再次得到了答案,从心出发,行云流水,大道至简。那些炫技,投其所好,矫揉造作的书写始终走入不了人心的深处。
一个雨天,我来到腾冲市,从界头乡回城的途中,特意拜访了那个让我心系多年的油灯庄。秋云打着伞在路口等着我,像一株荷花。油灯庄的房屋现已空无一人,秋云姐妹几个每段时间都会回来清扫小住,我看到了屋外那块厚实的牌匾——“农民作家段培东故居”。很欣慰,段老师走了,我们还能在此瞻仰他曾经的生活场所。斯人远逝,精神永存。走进段老师的故居,我居然没有丝毫的陌生感,归家一般,打开窗,拂去尘,行走于每间房。窑洞里,依旧保持着原来的模样,仿佛他耕田未归。我仔细地看着记录他生前点滴的展板,跌宕起伏的一生都被囊括于这逼仄的空间里,日常生活,军旅生涯,牢狱之灾,所获荣誉……在这平静的展示背后是一个农民作家激荡风云的奋斗史。他的一句话直击我心:“脚踏暗海催龙吟,笔底狂飙令虎啸。”也只有段老师,才配得上如此风雷激荡的气概。
房屋外面便是村文化活动室,几个老人坐在那里聊天——庄稼活路,人情来往,子孙前程,天南海北。他们的言语密如细雨,滋养着各自生活的田地。我想,段老师也在安静地聆听吧,乡亲们都在,真好。
到腾冲,很多人都会慕名前来段老师的故居,它已成为了人们瞻仰家国情怀,民族气节的精神高地。我想到了秋云的那段书写,这是作为女儿对父亲最深切的仰望:“人们关注一个农民作家的故居,其实就是关注我们这个民族的风骨和传承。父亲虽已远去,他的名字,他的风骨,将融入汗青,振奋民族精神,激励千秋万代,从今往后,滇云深处油灯庄村头的那盏曾经耀眼的油灯,将化作天边一抹明灭而恒存的星光,牵引着家国一方的刻骨铭心的历史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