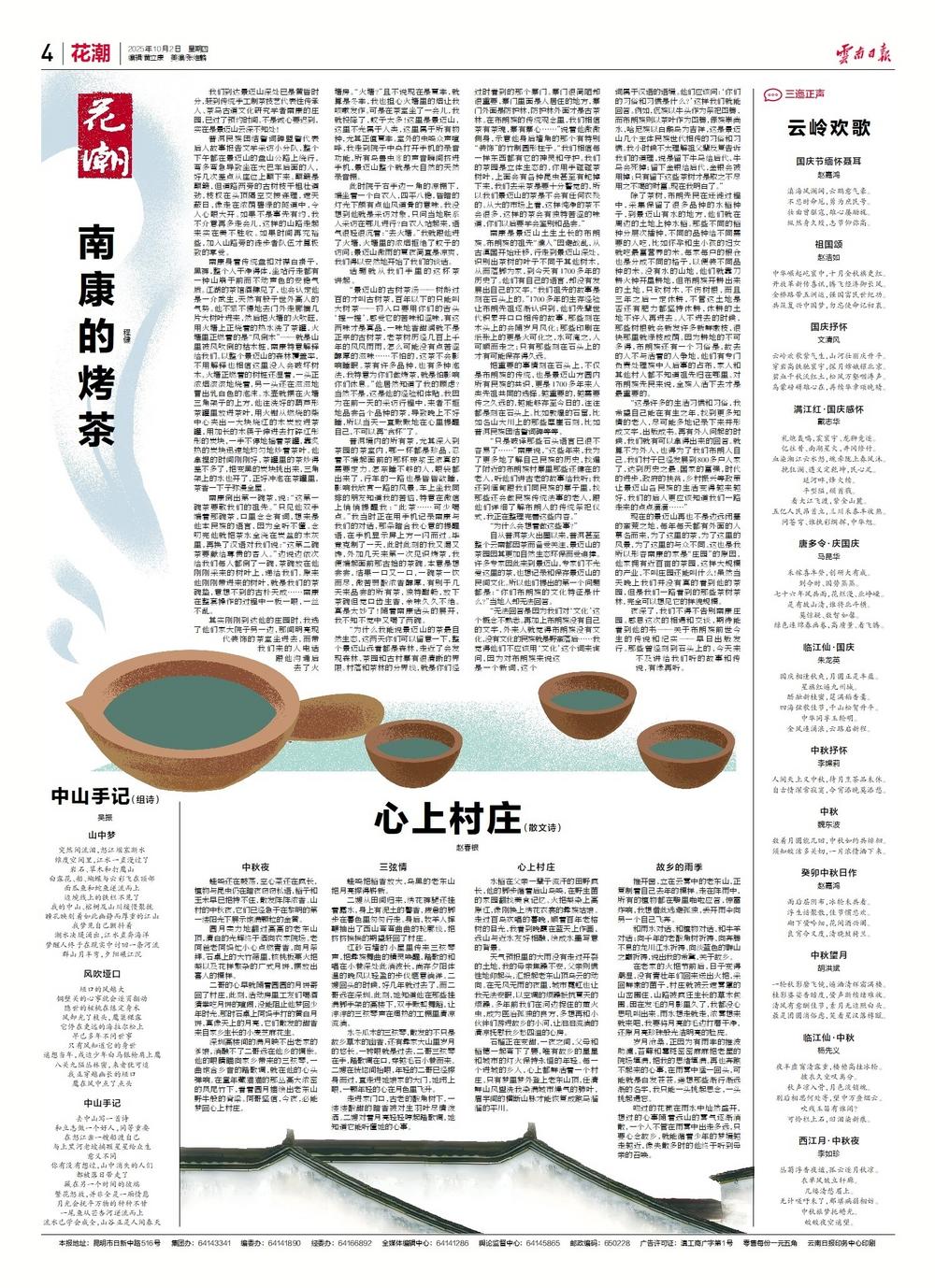程健
我们到达景迈山深处已是黄昏时分,赶到传统手工制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茶马古道文化研究学者南康的庄园,已过了预约时间。不是诚心要迟到,实在是景迈山云深不知处!
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盟誓代表后人故事报告文学采访小分队,整个下午都在景迈山的盘山公路上绕行,弯多弯急导致坐在大巴车后面的人,好几次差点从座位上颠下来。颠簸是颠簸,但道路两旁的古树枝干粗壮遒劲,枝杈在头顶隔空交接连理,遮天蔽日,像走在浓荫碧绿的隧道中,令人心眼大开。如果不是事先有约,我不介意再多走会儿,这样的山路走起来实在美不胜收。如果时间再充裕些,加入山路旁的徒步者队伍才算极致的享受。
南康身着传统盘扣对襟白褂子,黑裤,整个人干净得体,坐站行走都有一种山崩于前而不动声色的安稳气质。江湖的茶馆酒肆见了,也会认定他是一介武生,天然有股子世外高人的气势。他不紧不慢地去门外走廊摘几片大树叶进来,然后把火塘的火吹旺,用火塘上正烧着的热水洗了茶罐,火塘里正燃着的是“风倒木”——就是山里被风吹倒的枯木桩,南康特意解释给我们。以整个景迈山的森林覆盖率,不用解释也相信这里没人会破坏树木。火塘正燃着的树桩还湿着,一头正浓烟滚滚地烧着,另一头还在滋滋地冒出乳白色的泡沫。水壶就摆在火塘三角架子的上方,他往洗好的葫芦形茶罐里放进茶叶,用火钳从燃烧的柴中心夹出一大块烧红的木炭放进茶罐,用加长的木筷子伸进去打碎红彤彤的炭块,一手不停地摇着茶罐,靠炙热的炭块迅速地均匀地炒着茶叶。他拿捏的时间刚刚好,茶罐里的茶炒得差不多了,把变黑的炭块挑出来,三角架上的水也开了,正好冲泡在茶罐里,茶香一下子弥漫全屋。
南康倒出第一碗茶,说:“这第一碗茶要敬我们的祖先。”只见他双手端着那碗茶,口里念念有词,想来是他本民族的语言,因为全听不懂。念叨完他就把茶水全浇在炭盆的木灰里,再换了汉语对我们说:“这第二碗茶要献给尊贵的客人。”边说边依次给我们每人都倒了一碗,茶碗放在他刚刚采来的树叶上,递给我们。原来他刚刚带进来的树叶,就是我们的茶碗垫,意想不到的古朴天成……南康在整套操作的过程中一板一眼,一丝不乱。
其实刚刚到达他的庄园时,我选了他们家大院子另一边,那间明亮现代装饰的茶室坐进去,而带我们来的人电话跟他沟通后去了火塘房。“火塘?”且不说现在是夏季,就算是冬季,我也担心火塘里的烟让我咳嗽发作。可是在茶室坐了一会儿,我就投降了,蚊子太多!这里是景迈山,这里不光属于人类,这里属于所有物种,尤其正值夏季。室外的虫鸣众声喧哗,我走到院子中央打开手机的录音功能,所有鸟兽虫豸的声音瞬间挤进手机,景迈山整个就是大自然的天然录音棚。
此时院子右手边一角的凉棚下,端坐着一个白衣人,四平八稳,昏暗的灯光下颇有点仙风道骨的意味。我没想到他就是采访对象,只问当地联系人采访在哪儿进行?白衣人站起来,语气很轻很沉着:“去火塘。”我就跟他进了火塘,火塘里的浓烟拒绝了蚊子的访问;景迈山微雨的夏夜简直是凉爽,我们得以安然地开始了我们的谈话。
话题就从我们手里的这杯茶讲起。
“景迈山的古树茶汤——树龄过百的才叫古树茶,百年以下的只能叫大树茶——初入口要用你们的舌头‘搓一搓’,感受它的苦味和涩味,有这两味才是真品,一味地香甜润就不是正宗的古树茶,老茶树历经几百上千年的风风雨雨,怎么可能没有点苦涩醇厚的滋味……不怕的,这茶不会影响睡眠。茶有许多品种,也有多种泡法,我特意为你们做烤茶,就是怕影响你们休息。”他居然知道了我的顾虑?当然不是,这是他的经验和体贴。我因为在前一天的采访行程中,来者不拒地品尝各个品种的茶,导致晚上不好睡,所以当天一直默默地在心里提醒自己,不可以再“贪杯”了。
普洱境内的所有茶,尤其深入到茶园的茶室内,哪一杯都是珍品,忍着不端起面前的那杯琼浆玉液真的需要定力。怎奈睡不够的人,眼袋都出来了,行车的一路也是昏昏欲睡,影响我欣赏一路的风景。车上坐我同排的朋友知道我的苦恼,特意在微信上悄悄提醒我:“此茶……可少喝点。”我当时正在用手机记录南康与我们的对话,那条暗合我心意的提醒语,在手机显示屏上方一闪而过。毕竟克制了一天,此时此刻的我又渴又馋,外加几天来第一次见识烤茶,我便端起面前那古拙的茶碗。本意是想尝尝,结果一口又一口,一碗茶一饮而尽,微苦弱酸浓香醇厚,有别于几天来品尝的所有茶,独特酣畅,放下茶碗但觉口齿生香,余味久久不绝。真是太妙了!随着南康话头的展开,我不知不觉中又喝了两碗。
“为什么我能说景迈山的茶最自然生态,这两天你们可以留意一下,整个景迈山远看都是森林,走近了会发现森林、茶园和古村寨有很清晰的界限。村落和茶林的分界线,就是你们经过时看到的那个寨门。寨门很简陋却很重要,寨门里面是人居住的地方,寨门外面是防护林,防护林外面才是古茶林。在布朗族的传统观念里,我们相信茶有茶魂,寨有寨心……”说着他微微侧身,示意他身后墙角的那个有特别“装饰”的竹制圆形柱子。“我们相信每一样东西都有它的神灵和守护。我们的茶园是立体生态的,你用手碰碰茶树叶,上面会有各种昆虫甚至有蛇掉下来,我们去采茶是要十分警觉的,所以我们景迈山的茶是不会有任何农残的。从大的市场上看,这样纯净的茶不会很多,这样的茶会有独特苦涩的味道,你们以后要学会鉴别和品尝。”
南康是景迈山土生土长的布朗族。布朗族的祖先“濮人”因避战乱,从古滇国开始迁移,行走到景迈山深处,识别出茶树的叶子不同于其他树木,从而落脚为家,到今天有1700多年的历史了。他们有自己的语言,却没有发展出自己的文字。“我们祖先的故事是刻在石头上的。”1700多年的生存经验让布朗先祖逐渐认识到,他们先辈世代积累并口口相传的故事,那些刻在木头上的会随岁月风化;那些印刷在纸张上的更是火可化之,水可淹之,人可顺而走之;只有那些刻在石头上的才有可能保存得久远。
把重要的事情刻在石头上,不仅是布朗族的传统,也是景迈山方圆内所有民族的共识,更是1700多年来人类先祖共同的选择。越重要的,越需要传之久远的,越能够存至今日的,往往都是刻在石头上。比如敦煌的石窟,比如名山大川上的那些摩崖石刻,比如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等等。
“只是破译那些石头语言已很不容易了……”南康说,“这些年来,我为了更多地了解自己民族的历史,找遍了附近的布朗族村寨里那些还健在的老人,听他们讲古老的故事给我听;我还到缅甸跟我们同民族的寨子里,找那些还会做民族传统法事的老人,跟他们详细了解布朗人的传统祭祀仪式,我正在整理完善这些内容。”
“为什么会想着做这些事?”
自从普洱茶火出圈以来,普洱甚至整个云南都因茶而备受关注,景迈山的茶园因其更加自然生态环保而受追捧。许多专家因此来到景迈山,专家们不光爱这里的茶,也想记录和保存景迈山的民间文化。所以他们提出的第一个问题都是:“你们布朗族的文化特征是什么?”当地人却无法回答。
“无法回答是因为我们对‘文化’这个概念不熟悉。再加上布朗族没有自己的文字,外来人就觉得布朗族没有文化,没有文化的民族就是野蛮落后……我觉得他们不应该用‘文化’这个词来询问,因为对布朗族来说这是一个新词,这个词属于汉语的语境。他们应该问:‘你们的习俗和习惯是什么?’这样我们就能回答。例如,佤族以牛头作为祭祀图腾,而布朗族则以茶叶作为图腾,傣族崇尚水,哈尼族以白鹇鸟为吉祥,这是景迈山几个主体民族世代相传的习俗和习惯。我小时候不太理解祖父辈反复告诉我们的道理,说是留下牛马给后代,牛马会死掉;留下金银给后代,金银会被用掉;只有留下这些茶树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富。现在我明白了。”
除了茶树,布朗先民在迁徙过程中,采集保留了很多品种的水稻种子,到景迈山有水的地方,他们就在周边的土地上种水稻。那些不同的稻种分层次播种,不同的品种给不同需要的人吃,比如怀孕和生小孩的妇女就吃最富营养的米。每家每户的粮仓也是分成不同的格子,以便装不同品种的米。没有水的山地,他们就靠刀耕火种开垦耕地,但布朗族开耕出来的土地,只砍树木,不伤树根,而且三年之后一定休耕,不管这土地是否还有肥力都坚持休耕,休耕的土地不许人再进去。人不进去的时候,那些树根就会新发许多新鲜嫩枝,很快那里就绿枝成荫。因为耕地的不可多得,布朗族还有一个习俗是,故去的人不与活着的人争地,他们有专门负责处理族中人后事的占布,家人和其他村人都不知道祖先归在哪里。对布朗族先民来说,全族人活下去才是最重要的。
“这是许多的生活习惯和习俗,我希望自己能在有生之年,找到更多知情的老人,尽可能多地记录下来并形成文字,出版成书。再有外人问起的时候,我们就有可以拿得出来的回答。就算不为外人,也得为了我们布朗人自己。我们村子已经发展到800多户人家了,达到历史之最。国家的富强,时代的进步,政府的扶贫,乡村振兴等政策让景迈山各民族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好,我们的后人更应该知道我们一路走来的点点滴滴……”
现在的景迈山再也不是边远闭塞的蛮荒之地,每年每天都有外面的人慕名而来,为了这里的茶,为了这里的风景,为了这里的与众不同。这也是我所以形容南康的家是“庄园”的原因,他家拥有近百亩的茶园,这样大规模的产业,不叫庄园还能叫什么!虽然当天晚上我们并没有真的看到他的茶园,但是我们一路看到的那些茶树茶林,完全可以想见它的样貌规模。
夜深了,我们不得不告别南康庄园。感恩这次的相遇和交谈,期待能看到他的书——关于布朗族前世今生的传说和纪实——早日出版发行。那些曾经刻到石头上的,今天来不及讲给我们听的故事和传说,有缘再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