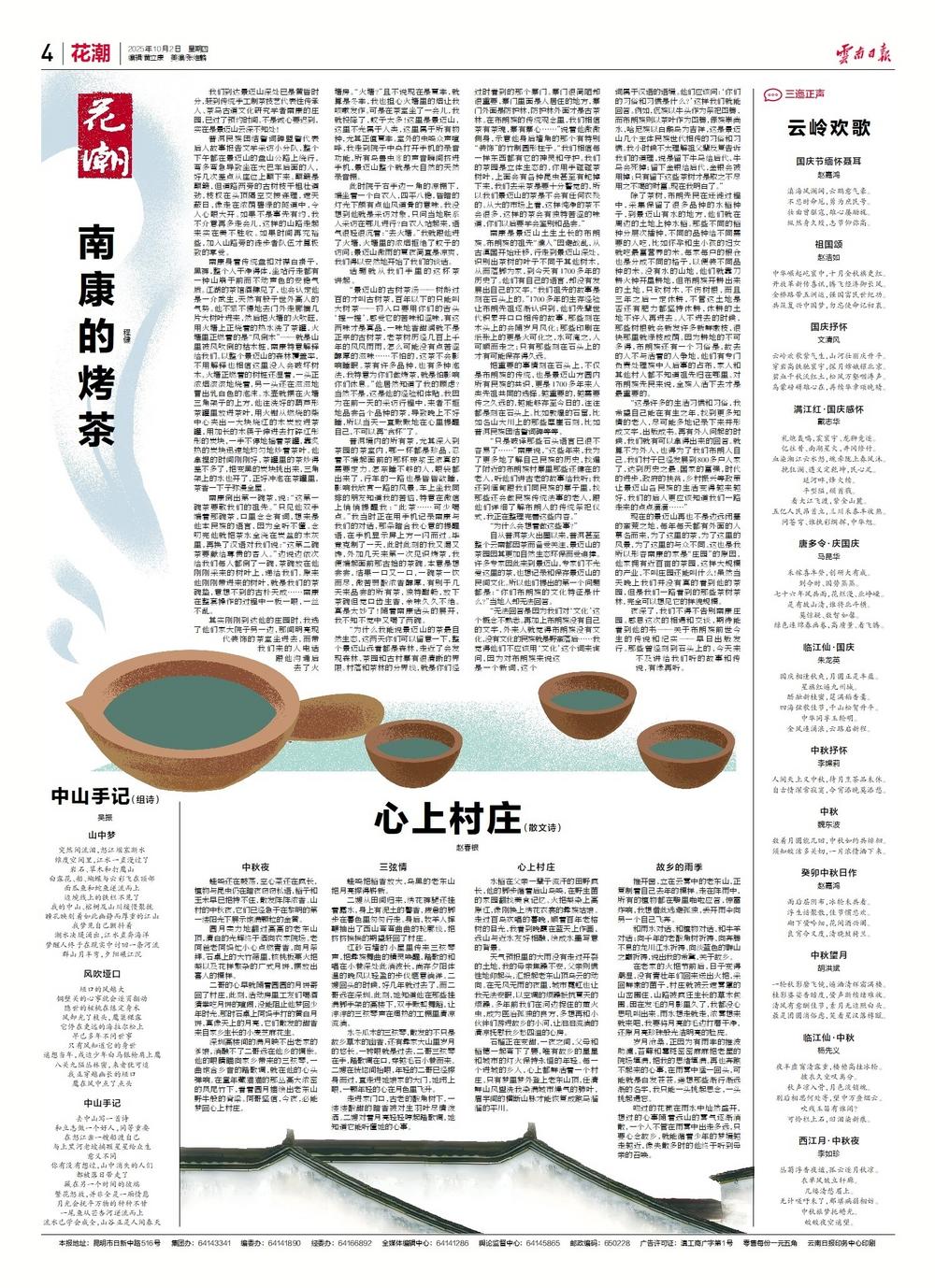赵春银
中秋夜
蛙鸣还在鼓荡,空心菜还在疯长,植物与昆虫仍在暗夜窃窃私语,稻子和玉米早已把持不住,散发阵阵浓香。山村的中秋夜,它们已经急于在黎明的第一缕阳光下展示饱满颗粒的金黄。
圆月卖力地翻过高高的老东山顶,清白的光辉终于洒向农家院场。老阿爸老阿妈忙小心点燃青香,向月祭拜。石桌上的大竹筛里,核桃板栗火把梨以及花样繁杂的广式月饼,摆放出喜人的模样。
二哥的心早就随着圆圆的月饼寄回了村庄,此刻,活动房里工友们喝酒猜拳吃月饼的喧闹,没能阻止他梦回少年时光。那时石桌上阿妈手打的黄白月饼,真像天上的月亮,它们散发的甜香来自家乡生长的小麦芝麻花生。
深圳高楼间的满月映不出老家的爹娘,消融不了二哥远在他乡的惆怅。他的眼睛瞄向家乡带来的三弦琴,一曲饱含乡音的踏歌调,就在他的心头弹响。在童年藏猫猫的那丛高大浓密的凤尾竹下,看着圆月描绘出老东山野牛般的脊梁。阿哥坚信,今夜,必能梦回心上村庄。
三弦情
蛙鸣把稻香放大,乌黑的老东山把月亮擦得崭新。
二嫂从田间归来,绣花裤腿还挂着露水,身上有泥土的馨香,疲惫的脚步在暮色里匆匆行走。身后,牧羊人挥鞭抽出了西山弯弯曲曲的轮廓线,把挤挤挨挨的期望赶回了村庄。
红砂石墙的小屋里传来三弦琴声,把彝族舞曲的精灵唤醒,踏歌的和唱在小巷深处此消彼长,尚存夕阳体温的晚风以轻盈的步伐惬意徜徉。二嫂回头的时候,好几年就过去了,而二哥远在深圳。此刻,她知道他在那些挂满脚手架的高楼下,双手默契舞蹈,让淙淙的三弦琴声在燠热的工棚里清凉流淌。
水冬瓜木的三弦琴,散发的不只是故乡草木的幽香,还有彝家大山里岁月的悠长。一转眼就是过去,二哥三弦琴在手,踏歌调在口,穿越毛石小巷而来。二嫂在恍惚间抬眼,年轻的二哥已经擦身而过,直走进她娘家的大门,她闭上眼,一颗年轻的心在月色里飞升。
走进家门口,古老的酸角树下,一缕缕酸甜的暗香被对生羽叶尽情泼洒。二嫂对着月亮轻轻哼起踏歌调,她知道它能听懂她的心事。
心上村庄
水稻在父亲一辈子流汗的田野疯长,他的脚步循着后山鸟鸣,在野生菌的家园翻找美食记忆。火把梨染上高原红,像刚换上绣花衣裳的彝族姑娘。走过百鸟欢唱的暮晚,顺着百年老榕树的目光,我看到晚霞在蓝天上作画,远山与近水友好相融,绘成水墨写意的背景。
天气预报里的大雨没有走过开裂的土地,我的母亲焦躁不安,父亲则惯性地仰起头,汇报起老东山顶乌云的动向。在无风无雨的夜里,城市霓虹也让我无法安眠,以空调的烦躁抵抗夏天的烦躁。多年前我们在河边捉住的萤火虫,成为医治孤独的良方,多想再和小伙伴们游进故乡的小河,让汩汩流淌的清凉抚慰我乡愁四溢的心房。
石榴正在变甜,一夜之间,父母和稻穗一起弯下了腰,唯有故乡的星星和城市的灯火保持永恒的年轻。每一个进城的乡人,心上都鲜活着一个村庄。只有梦里梦外登上老东山顶,任清鲜山风盥洗我染满城市燥气的肺叶,眉宇间的横断山脉才能恢复成跑马溜溜的平川。
故乡的雨季
推开窗,立在云雾中的老东山,正复制着自己去年的模样。走在阵雨中,所有的植物都在噼里啪啦应答,惊雷炸响,我想借此逃避孤独,丢开雨伞向另一个自己飞奔。
和雨水对话、和植物对话、和牛羊对话;向千年的老酸角树祈祷、向奔腾不息的龙川江水祈祷、向淡蓝色的群山之巅祈祷,说出我的希冀,关于故乡。
在老家的火把节前后,日子变得潮湿,没有青壮年们回来送出火把,采回鲜嫩的菌子,村庄就被云遮雾罩的山峦围住,山路被疯狂生长的草木包围。困在发毛的月影里久了,我都没心思吼叫出来。雨水想走就走,浓雾想来就来吧,我要将月亮的毛边打磨干净,还原月亮珍珠般光洁明亮的脸庞。
岁月沧桑,正因为有雨季的推波助澜,苔藓和霉斑密密麻麻把老屋的院场填满,把我的思绪填满。再也奔跑不起来的心事,在雨雾中猛一回头,可能就是白发苍苍。遥想那些渐行渐远渐的名字,我只能一头挑起思念,一头挑起遗忘。
吻过的花苞在雨水中灿然盛开,想过的心事随着远山的雾气逐渐消散,一个人不管在雨雾中出走多远,只要心念故乡,就能循着少年的梦境越走越近,像失散多时的他终于听到母亲的召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