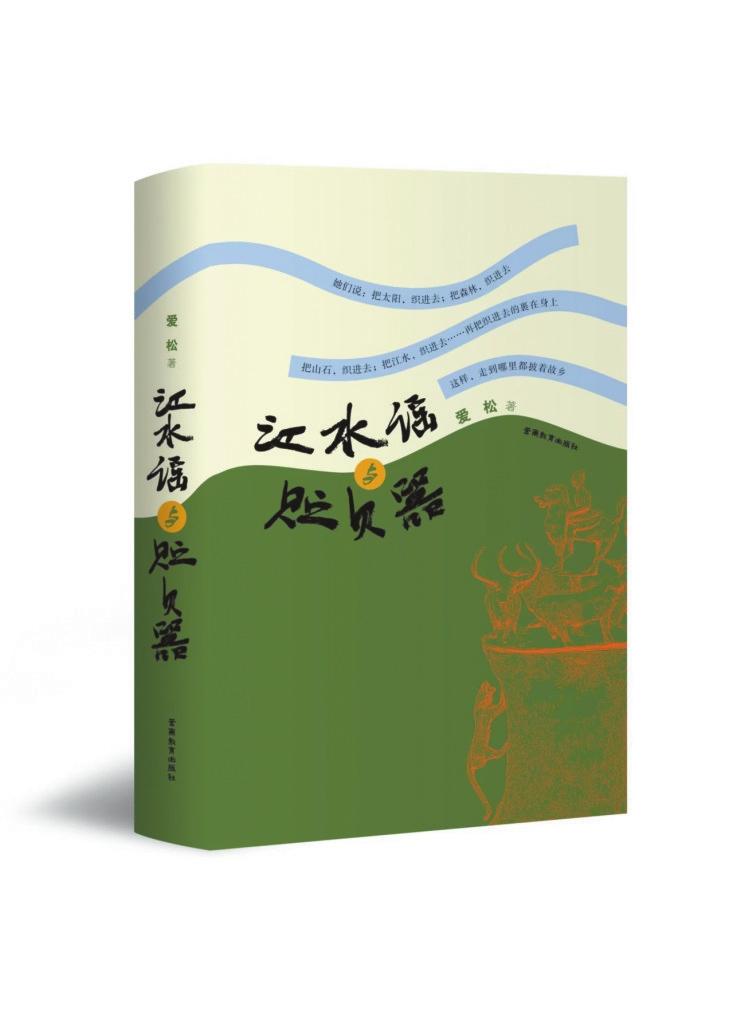高秀芹
当我在北京的酷暑中收到来自七彩云南的诗人爱松的诗集《江水谣与贮贝器》时,来自精神世界的某种启示如清风徐来,一本奇异的诗歌样本召唤着陷入困顿和焦虑中的僵化躯体与疲倦精神。如同江水谣的清澈与贮贝器般的神秘,两种完全不同的审美体验所带来的两股潜藏力量,赋予这本诗集两种或者多种混杂的“调性”。也正是这种内在的多样性与张力,使得阅读过程充满激情与挑战。
诗人富有创见地找到了两个容纳力和涵盖力超强的意象——“江水谣”的轻与“贮贝器”的重。水的柔与金属的硬,简单的呈现与繁复的发展,人生或人类的初始状态与波澜壮阔的叙事风格,这些对立而又统一的美学元素,共同构建出一个既冲突又和谐的诗歌宇宙。它超越了我所阅读过的许多诗歌作品所带来的感受力,复活了我某些休眠的感官与对生命的领悟。感谢这部风格对立又彼此共鸣的诗集,其旋律如此妙不可言——纯粹的,简单的,繁复的,混杂的,一切仿佛天成,又处处可见匠心。
“江水谣”理应是动的,一切的水都是流动的,波折而富有变化。但有趣的是,在爱松的诗歌中,“江水谣”所呈现的美学反而是静的。它如同世界的起源,如创世纪一般,山、水、日、月仿佛本来就在那里,然后“人”才出现——人看,人感受,借诗人的眼睛来描述存在的现实。这样的诗歌近乎哲学,富有人类初始状态的生态与自然美学,更是一种“静”的完整体现。
且看第一首诗《问》:
“听到我叫你了吗?”
高黎贡山在东边问
“瞧得见我找你么”
担当力山在西边说
我无法回答
被巨石截挡的血液
沿着河床咆哮
这不是屈原的《天问》,而是诗人的“问天”,是“问山”。两座山,两个人,两颗心,在自然之上、大地之上彼此呼唤,却被大河截挡。那咆哮的河水,仿佛是被阻挡的血液,是悲情的宣泄。山不仅是身体,还是心灵;水不仅是流动,更是情感的奔涌。山与山在倾诉,山与水在默契。诗人帮助我们谛听并撰写这一切,自然生态本是鲜活、动态的,但诗歌的美学与调性却赋予其一种深沉的宁静感,仿佛摹写天地万物,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是一种语言创世的美学实践。
诗人生存的天地万物中,有大山大河,有蜜蜂蝴蝶,有植物与语言,有生生不息的江水,有江水无限变化的样态:“我更相信/它们,是石头变来的/或湍急或平缓中/没人指得出一个确切位置/安放瞬间翻腾:/它们有着人鱼面具/也有铁石心肠。”(《水》)水如此之硬,如点鱼成石,水中万物皆空,在有无之间流转。“江水谣”部分共收录50首短诗,其中30首的题目仅为一个字,如初始的命名,摹写自然与天地万物,动中有静,静中见动。静,在此成为存在的全部,是诗人对世界本质的深刻凝视。
这一现象极为耐人寻味:为什么本应流动的“江水谣”,反而呈现了一种静的美学?而与之相反的是,“贮贝器”如同青铜化石般凝固、静止,但打开之后,却是滚动的情绪与记忆。沧海桑田,波涛汹涌,人流滚滚而来,音乐曲调高低回旋,祝福与祈祷交织,一个家族逐渐浮现:父亲、母亲、哥哥、姐姐、弟弟,还有一个穿梭其中的“我”。每一个身份、每一滴血液中流淌的家族历史、承担与功能,都在“贮贝器”中被雕刻、被封存,一旦打开,便如洪水般涌来,成为一个家族、一个族群创世纪的叙事诗。“贮贝器”是历史与记忆的化石,它是宁静的,在美学上恰恰是浩瀚波动和无限动态的。
这真是一个玄妙的现象。诗人尝试在叙事长诗中创造家族的冲动与野心,每一个血缘身份都承担着各自的使命,家族史实则也是“古滇国”的兴衰史。在中国当代诗歌中,叙事诗并不丰富。诗歌的叙事与小说的叙事是截然不同的两种风格。小说天然适合讲故事,人与家族的叙述在小说中容易展开,但在诗歌中却极为困难。西方的长诗,如《浮士德》与《唐璜》,倒是为叙事与抒情的结合提供了卓越的样本。回到中国当代新诗的语境中,叙事长诗的写作难度更大,而爱松的“贮贝器”恰恰提供了一个难能可贵的写作样本。
我没有细数“贮贝器”具体有多少诗行,但240多个页码已足以见其宏大规模。诗人以精巧的叙述节奏,配合不同社会身份的切换,使长诗在抒情与叙事之间保持了一种微妙的平衡。每个角色出场前都有一首“导诗”,如导诗一“惊愕”引出与“父亲”有关的内容。这些“导诗”部分均以著名作曲家的音乐作品命名,如“惊愕”源自海顿G大调第九十四交响曲。诗人深谙音乐,如此大胆的运用可谓用心良苦,既是对古典音乐的致敬,也是以高蹈而丰富的音乐性来诠释“贮贝器”的内在精神。在“贮贝器”表面看到各种奇异的动物和纹饰,打开后却是神秘的家族历史。家族和历史,精神和骨头,与“再把影子作为你的面具/装扮成一座,发光的城”的哥哥不同,弟弟则要建立新的乐曲规则和秩序:如何让这个家族的老屋,成为南玄村;/如何让南玄村,成为晋虚城;如何/让晋虚城,成为古滇王国/如何让古滇王国,成为/真正家族和自己的过去……平衡的生与死,精神和骨头,硬和软,家族中每一人的命运和劫数,记忆发着光有声有响,从一个凝固的东西成为一个流动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动和静在这个诗集中是非常玄妙的一个存在,也是它的一种特殊的美学。
在诗之结尾,诗人写道:“一个家族对命运,和一个王国对命运,/几乎是等同的,晋虚城,/不过只是两者之间,/被大乐队演奏的一座墓碑之石。它久远的消失,并未超过它/短暂的存在。”此句堪称绝妙,不仅收束了长篇的叙事,更在哲学层面上提升了诗歌的意境,令人回味无穷。
“江水谣”部分均为短诗,短诗之简单、纯粹、无我,体现出一种减法的美学。而“贮贝器”作为长诗,则含混、复杂,诗人以诗歌叙述家族的命运,极具抱负与理想——并且实实在在地达到了预期的效果。诗歌作为一种抒情性极强的文体,用来表达家族与历史的命运,本就艰难。我已经很久没有读到如此具有穿透力和完成度的长诗了。
如果我们用颜色来描绘《江水谣与贮贝器》,诗人有意识地写道,在“贮贝器”中“祈祷黑色,多于白色”。那么,“江水谣”恰恰相反,可以说是“祈祷白色,多于黑色”。白与黑,皆是一种纯粹。诗人在诗歌中达到了浑然一体的纯粹——不论是在短诗中所实现的“白”,还是在长诗中所铺陈的“黑”,时空交错,最终都抵达了某种“抵达”:抵达,也是“江水谣”的一首:
丈量双脚的绿
顷刻碾过车轮的红
穿梭梦境,默默盛放的紫
没什么能带得走
山顶的落雪
长满皱纹的水花
以及,闷声不响的亡灵
绿、红、梦境的紫、山顶的落雪、长满皱纹的水花……诗人以纯粹和静止的“白”,打开记忆之门的幽暗深邃的“黑”,这正是“贮贝器”的诗歌内涵。两者形成互文镜像,彼此照耀,共同构建出一幅完整的精神图景。
爱松通过《江水谣与贮贝器》完成了一次诗学上的冒险,也是一次精神上的返乡。爱松以轻灵之笔写就沉重历史,以沉默之物唤醒轰鸣之声。他用语言重建了一个世界,既是对古滇文化的追忆,也是对现代人精神处境的回应。诗集中的每一首诗,不仅是文字的排列,更是情感的考古、记忆的仪式。在这个意义上,爱松不只是在写诗,更是在进行一种文化的贮存与传递——正如贮贝器本身的功能,封存的是时间,开启的是永恒。这部诗集证明,诗歌可以在凝固与流动、纯粹与复杂、个人与史诗之间,建立一座隐秘而永恒的桥梁。它不仅是语言的创造,更是一种精神的贮存与流传——奇异,而直抵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