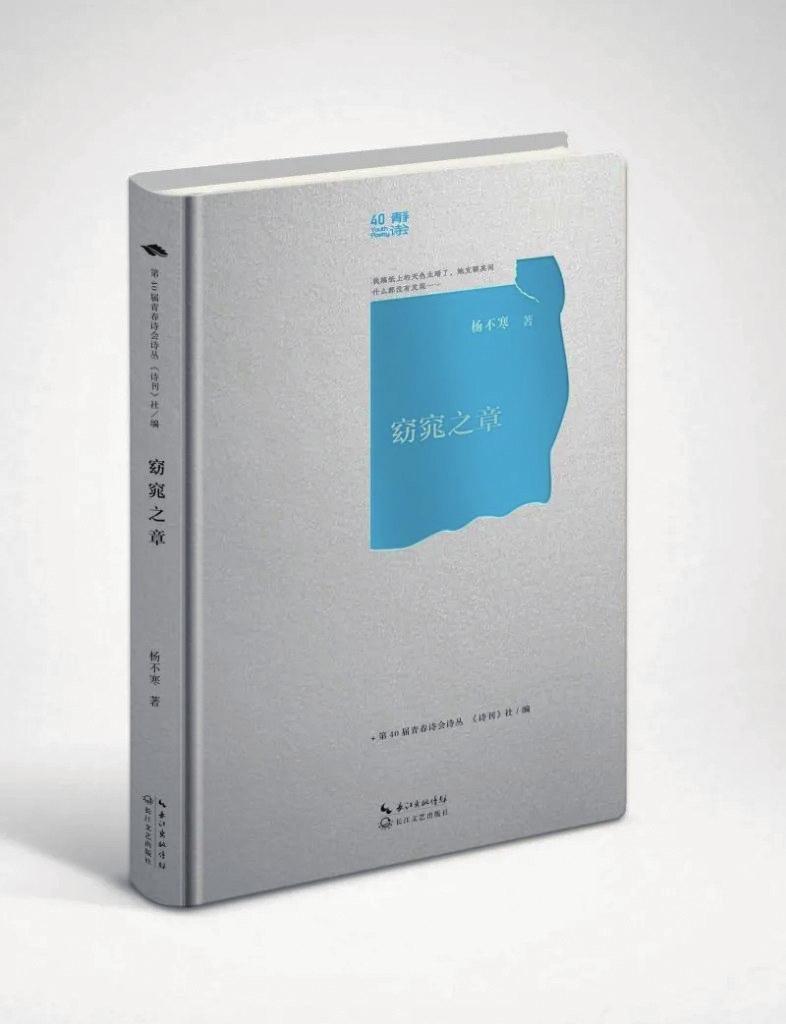何飞龙
自新诗诞生以来,向西方诗歌学习一直是现代汉语新诗艺术探索的重要路径。然而,使现代汉语新诗保持“汉语的”民族特性,则关涉诗人如何有效地“继承”中国古典诗学资源。诗人杨不寒的诗歌创作,体现出显著的现代生命经验与历史文化有机融合的自觉意识。在他的诗歌创作中,大量充满古朴气息的古典意象扑面而来。杨不寒的写作如同驾驶一艘夜航船,在墨色的海洋上与那些闪烁于人类文明史的历史人物相遇,抚摸彼此的心灵。
杨不寒致力于激活古典,从而探寻其当代表达的可能性。故而,在杨不寒的诗作中,可以看到既隐身又现身的自我形象。在他以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为抒写对象的作品中,常表现出对“题材”实践功能的超越,从而构建起一种独特的认识历史的诗歌视角。这种对历史的透视与回望,是一种非线性的叙述,而是将历史文化记忆与当下生命经验进行有机整合,是一场回归古典的审美之旅。在长诗《窈窕之章》中,杨不寒将“巫山神女”的典故巧妙地移植在当代女性身上,在解构古典诗歌意象的过程中洞察当代女性的生命困境。诗中的“她”看似被冠以“现代神女”的称号,其命运却是被水草缠绕周身。在“她”努力“扯断周身水草”的抗争中,却遭受来自生活的重重围堵,便对象征永恒的“石化神女”萌生质疑:“她越来越怀疑所谓传奇,只是一堆/虚构的石头,所以自己才得不到真实的安慰/与庇护”。在这首艺术性与思想性俱佳的长诗中,通过对古典意象的现代性转述,杨不寒对以诗中“她”为代表的现代女性生存困境进行呈现:即“在虚空中飞升”的同时“在掉色的倒影里/不断沉下去”。
杨不寒对古典诗歌传统有着深入理解,在继承古典的同时进行自我内化,赋予其全新的现代性内涵。因此,在《北碚,萧红的1939》中,杨不寒与1939年寓居重庆北碚的才女萧红,在相向而开的窗户前完成了穿越时空的“相认”:“隔着时间的江水,她的窗户/与我相向而开,仿佛在等着我/前来相认。”杨不寒常常以现代意识解构历史并对其进行想象性的重构,致使诗中的说话人“我”既成为历史的旁观者又成为参与者:“我在试管外,屏吸观察他/与楚南空气发生化学反应的过程”(《芰荷为衣·六》)。在中国文学史乃至整个中国文化史的叙述中,三闾大夫屈原被冠以忠君爱国、品性高洁等标签,这固然体现了屈子的伟大人格。然而,杨不寒则对历史进行还原并指认出一个真相:“诗人就是古老傩戏里/的一张悲剧脸谱”(《芰荷为衣·九》)。此外,陶渊明、嵇康、杜甫、苏轼等历史人物及其文化灵魂,在杨不寒的笔下均被重新激活,获得了当代意义。
黑格尔在《美学》中曾说过:“诗人必须从内心和外表两方面去认识人类生活,把广阔的世界及其纷纭万象吸收到他的自我里去,对它们起同情共鸣,深入体验,使它们深刻化和明朗化。”从杨不寒的诗作内容来看,他不断地将当下自我的心灵方寸与历史人物的精神内蕴进行对接。然而,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摆在读者面前:作为生活在现代的人如何穿越时空与古人进行一场灵魂的抚摸,如何延续古典诗歌的精神血脉?《“共云山”》一诗,或许给出了答案:
“共云山”
三峡楼台淹日月,五溪衣服共云山。
——杜甫《咏怀古迹五首·其一》
大历元年的日影下,月色下
老杜甫与五溪人一同作息
在我的峡江故家。两岸山岩陡如楼台
猿猴用手掌,给石灰岩的卯榫抛光
离开瞿塘以后,我搬进了
北碚的高楼。一夜一夜幻想
幻想钢筋拱起的建筑
也似危崖,时间的光影在马路上流淌
昨天下午,我走进社区超市
突然记起老杜甫也时常散步到山下
沽酒,买鱼。于是对水产区
那个面带愠怒的老人,多了几两敬意
凌晨,我梦见他在诗里放养的水云
已随我来到人世间
同我一起在大街上走动
也一起巢居于,城市的危崖上面
《咏怀古迹五首》是杜甫于“大历元年”(776年)在“夔州”(今重庆奉节)所写。千年后,来自重庆奉节的杨不寒以《咏怀古迹·其一》中的名句“三峡楼台淹日月,五溪衣服共云山”为引,在一种互文性写作中建构起别致的对话空间。诗作开篇用具体的时间“大历元年”和空间“日影下”“月色下”为历史赋形,将抽象的历史事件还原为一个具体的时空。杜甫也不再是一个“现实主义”爱国诗人的干瘪符号,而是与五溪人“共云山”立体的形象。然而,诗人并未滞于对历史的外在描述,而是用一句“在我的峡江故家”将古典与现代的界限消弭,让“我”与杜甫同处于一个交错的诗意空间。“猿猴”用手掌对陡峭如楼台的两岸山岩的榫卯抛光,则将自然景观进行人化,与第二节中的都市建筑形成呼应。
在第二节中,一个关于离乡寓居他处的生命课题被诗人抛出。当“我”的生活空间从“瞿塘”变成“北碚的高楼”后,生命经验与生活体验均已发生转变。“钢筋拱起的建筑/也似危崖”与第一节中陡如楼台的山岩形成诗意的圆环,寓居夔州的杜甫与身处北碚的杨不寒所面临的去乡后的生命感知再次产生共振。这种空间上的转变,带来了对时间敏锐的感悟:“时间的光影在马路上流淌”。诗人试图在时间的流动性中寻求与彼时杜甫精神意蕴上的共通性,也即“共云山”。概言之,身处异乡的杜甫在进行自我调适后寻获“五溪衣服共云山”,离开瞿塘进入都市生活的杨不寒也在寻求“北碚高楼共云山”。
诗歌的第三节将“我”与杜甫的生活经验的对接推向更深层。杨不寒提供了一种重新审视庸常生活的新视角,即在重复琐碎的生活中发现诗意。社区超市在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日常购物似乎彰显出某种反诗意。然而,逛超市这种带有重复性的行为,在诗人“突然记起老杜甫也时常散步到山下/沽酒,买鱼”后,具有了诗意的可能性。杨不寒将杜甫从文学史的圣坛拉回人间,他与当代一个普通的城市居民一样,需要纠缠于油盐酱醋。这种以生活为诗的态度,使“我”对水产区“那个面带愠怒的老人,多了几两敬意”。在重复且单调的购物中,潜藏在生活细节中的诗意被发现、激活,“我”与同样需要“沽酒,买鱼”的杜甫实现了一场跨时空的精神共鸣。
诗歌的结尾处,诗人以梦境将现实与超现实联结起来。杜甫在“诗里放养的水云/已随我来到人世间”,意味着诗人在古典与现代之间找到了可以承续的精神内核“水云”,这是一种具有流动性的自然现象。源自杜甫的“水云”在当下“同我一起在大街上走动”并最终与“我”“一起巢居于,城市的危崖上面”。“巢居”昭示着生活在现代都市的人的生命状态,宛若鸟一样。尽管城市化给人们带来诸多的便利,然而这种失乡后游魂般的命运遭际,则如同居住在“城市的危崖上面”一样危险。
整体看来,《共云山》一诗的内核在于“共”。诗中“危崖”一词出现两次,这表明杨不寒在诗作主题“共云山”之外,还对当下人们面临着的撕裂和矛盾生命境况进行了思索。在“共危崖”与“共云山”反向角力中,杨不寒提供了一种可供读者参照的审美路径。其一,杨不寒试图在现代都市生活的褶皱中,寻求诗意栖居的可能性,以实现日常生活与诗意栖居之“共”;其二,钢筋水泥丛林不应是充满灵性自然的对立面,在都市生活中打捞诗意以谋求他乡与故乡的空间之“共”;最后,生活在一个“诗意匮乏”的加速社会,那些历史中熠熠生辉的生命体或许能在一颗虔诚的诗心叩问下,进行一场跨越时空的心灵观照。
黑格尔在论述历史与诗的差别时认为,诗具有一种改造现成材料的自由,从而“使外在事物符合内在的真理”。这意味着,诗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叙述,通常是带着强烈主观意识的想象性重构,而非史学如其本然那般陈述客观的事实。杨不寒有着自觉的诗歌艺术追求,有意识地建构一座跨古今的桥梁,将古典与现代、历史与当下、个体生命经验与历史文化记忆联结起来,最终完成一次诗歌艺术的审美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