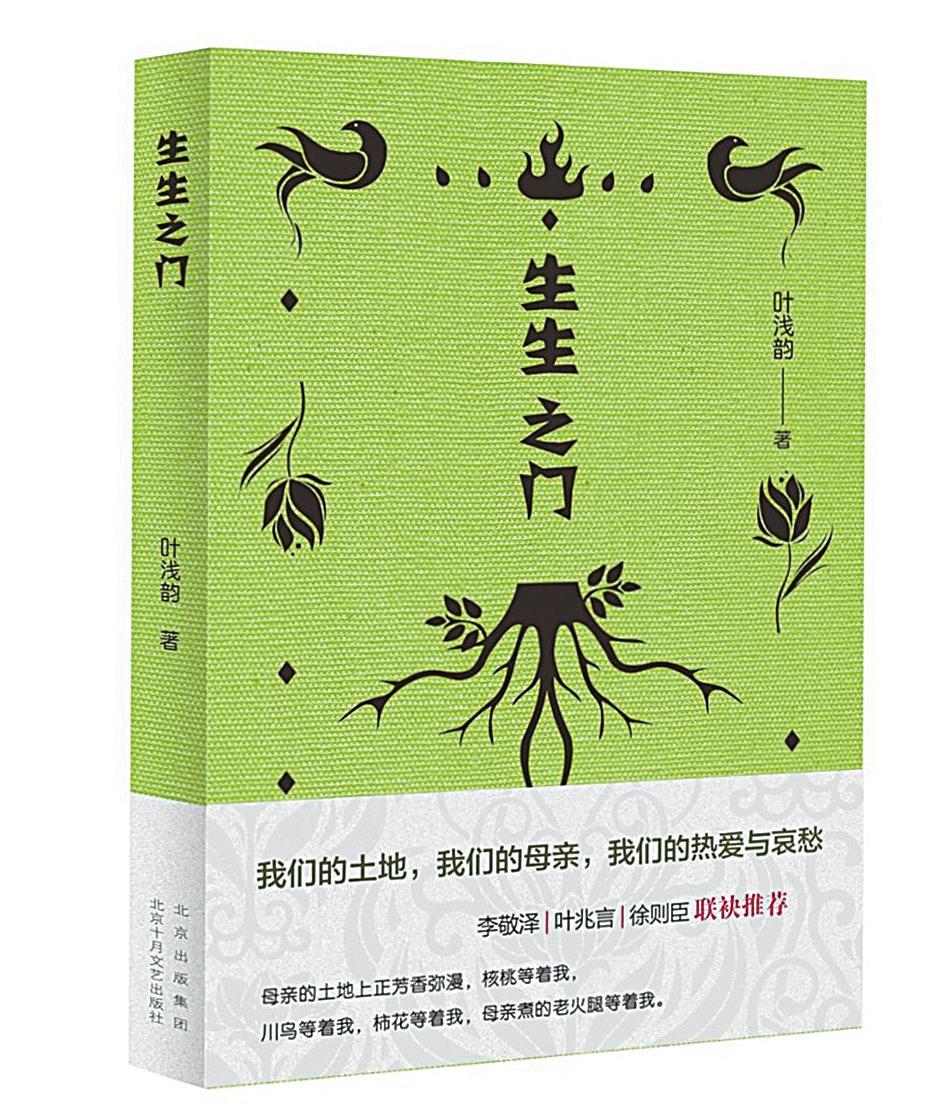陈庆颖
《生生之门》是叶浅韵生生系列散文的聚水成河。从生生之门、生生之木、生生之火,到生生之土、生生之金和生生之水,原汁原味地呈现出滇东北地区世居于此的人们极具原始爆发力的生存之景。每一篇独立成文,篇与篇之间又遥遥相应。这些遥相呼应的文字织出一张绵密的网,让我透过命运的微光看到生生不息的土地上睿智经营的母亲和一茬一茬的庄稼。我很纳闷:一个从小生长于鲁东南乡村的我,何以会对作者笔下的滇东北生活有着一种感同身受,这两者之间可是隔着千山万水的距离呀。
生儿育女繁衍后代在农村,尤其是在偏远山区,无论什么时候都是一个家庭甚至是一个家族的头等大事。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个“后”一般意义上理解为儿子。《生生之门》里生了儿子的二伯母家庭地位“明显高出了一篾片”,简直是“母凭子贵”的样板。文章从最初的多子多福写到后面的计划生育,再写到近年来的放开二胎,写到人们对生育的观念在跟着国家政策走。见到五伯母又生了个女儿的丈夫一面要拿粪箕将孩子端了丢出去,一面大声地对五伯母说:“你还趴着干什么,还不赶紧给我起来,该干嘛干嘛去。”这只认儿子不管不顾女人刚从鬼门关转回来的场面让人哽咽,忍不住心生悲凉。我随即想起另一个场景:10多年前,山东老家一位同事的母亲在得知儿媳妇临产时从百里外赶来,等看到生下的是个女娃,立马头也不回气呼呼地走掉了的场景。地域上虽是一南一北,但场面又是何其相似。深入想来,和叶浅韵在《生生之门》呈现的思考都是对人性的终极拷问。
一个又一个母亲为了家庭或家庭的繁衍像机器一样不停地生育,耗尽了青春与热情。滇东北地区的母亲如此,鲁东南的母亲如此,全中国的母亲大抵都是如此。她们倾其一生所有,为一家老小勉强活成里里外外一把手。她们对生活也有无数的委屈与不满。于是,婆媳之间,邻里之间,就有了这样那样的嫌隙,这样那样的心结。一个个母亲们便会使出自己的杀手锏,力气干不过别人,嘴巴上一定要盖过对方。村子里几个“被婆婆周治的媳妇,一聚在树荫下就骂家里那老不死的”;火灾之后,母亲“一边挑水,一边哭,一边咒”;深夜老鼠偷粮食,奶奶咒老鼠是“这些烂牙巴骨的死耗子”,仿佛咒骂上一通,身上的苦就轻了,心里的气就顺了,日复一日的生活就又继续向前。
从齐鲁大地远来求学继而扎根云南已10年有余的我,很多时候是以一个北方人的视角远远观望这“异域”文化的五彩缤纷。更多时候,我感受到的是南北地域在民风、民俗方面的巨大差异。我常常深感彩云之南在经济方面的落后,又惊叹民族文化方面的异彩纷呈。虽居于此地10年有余,自己的孩子也出生于此,可算得上是半个云南人了。只是,作为一个外来者,我工作在城市,极少深入乡村,深入一个一个淳朴无华的劳动者的内心,极少有机会与他们生活在一起,吃住在一起,我看得到的只是他们外在的服饰和迎面的笑容。叶浅韵的生生系列给我带来极大震撼的是,每一篇文章仿佛自带神功,轻易就打通了我的任督二脉,让我一下就倒在了这片富有魔性的土地上,一下子就热爱上滇东北地区的男女老幼,哪怕他们之中有些人有这样那样的毛病。我甚至热爱上了奶奶诅咒的偷粮食的小老鼠,它们在作者笔下完全组成了人与自然共处的和谐画面这片生养了作者的神性大地上,有各种各样的天灾人祸,有无数让孩子在参与大人的劳作同时发现的各种各样的乐趣,有为了生存下去与命运的各种各样的抗争。诚然,囿于环境的恶劣,世居于此的人们是要迎面各种苦难的,但这样的大地同时又是有血有肉、有泪有笑、有苦有乐的。那些个信手拈来的当地方言,让我这个外来户都忍不住成为铁粉了。外婆嘴中的“外孙是外狗,吃了往外走”和北方人说的“疼外甥,不如疼个破盖顶”简直是异曲同工呀;母亲的“你这个做贼不会盖脚迹窝的憨狗”读了直让人想象出活灵活现的画面;“丁丁糖,丁丁糖,吃了不想娘”这童谣一样的方言简直就是对无忧无虑童年生活的追忆与呼唤。
今夜,在床上翻来覆去的我被隔着几千公里地域差异的文字唤醒,又被这天南地北民间文化的共通性温暖。仿佛任是大江大河时空地域的切割亦不但不能割断我华夏几千年文明的血脉,反而助长了不同地域之间淳朴风俗的遥相呼应。在目标明确的现实面前,我常常自觉无比乏力,在柔情似水的文字面前,我又常常自觉满血复活,像阿Q,也像堂·吉诃德。这是文字在赋予沉重的肉身以精神的引擎,牵动我们不时地在半空中俯视生活。
生是我们来到这个世上的全部动力,无论乡村还是城市。乡村的风土人物尤其彰显着生的力量。一棵蒺藜能在沙子地上蔓延它坚韧的根茎,一朵牵牛花在杂草丛生的田间小路上活力绽放它优雅的青春,同样,一坨不但不臭还落地有型的牛粪安然地躺在地头等着有心的农人把它铲进自家田里。在叶浅韵的生生系列里,来自乡村的物事都是彪悍有力的。二伯母撕心裂肺的生产,人们在土里刨食的艰辛,无不彰显着生之艰难,生之伟力。文章常常让我忆起那些与土地直接打交道的日子。深秋的早晨,天还不亮,就被父亲母亲赶牲口一样的叫醒,一家老老小小赶到东山上收地瓜。挂着凉意的露珠聚在经霜的紫绿色叶子上,一垄一垄起伏在根据地势切割成不规则形状的田里。刨地瓜之前要把这些牵牵绊绊的瓜秧先扯掉。父亲抡起透着铁亮的䦆头在空中划一道优美的弧线,然后对着田垄深深地陷下去,一窝沾着泥土气息大小不一的红皮地瓜就浮出地面……
作者笔下的物事一样一样的,来自大山深处的田垄、篱笆、菜园,来自生生不息的祖辈、父辈与自己这一代,更来自“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文化的氤氲与反哺。都说,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山川阻隔一定程度上涵养成一个地域独特的方言与风土人情。同时,山川又从来也不能阻隔真正有情有义的地域文化的交流、交汇与交融。否则,人们便不能在面对同一部经典时发出如此一致的赞叹。有一千个观众,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人们心中的哈姆雷特某种意义上有所差异,但经典在人们心中激起的波澜却是惊人的一致的。如此看来,一个土生土长的云南人,写的是地地道道的云南生态物事,却在一个北方读者的心里撩拨起千沟万壑的情愫,也就不足为奇了。
许许多多从乡村长大的孩子,为了理想也好,为了生活也好,为了城镇化也好,纷纷远离了故土,来到高楼林立的城市。物质方面的生活诚然给了我们童年所不曾有的宽裕,精神层面我们却如同被驱逐出伊甸园一样,对曾经的故土一草一木越来越疏离,同时,又无法完全融入任何一个南来北往人群汇聚而成的城市。浮萍一样的心绪并不比亡国被俘时的文天祥少一丝一毫。漂泊无依的细浪时时涌上心头,令人在灯火辉煌的城市加倍思念伸手不见五指的故乡。似乎偶尔还能隐隐听到童年跳房子、打老红、掏鸟蛋、偷粽叶、爬墙上屋时的欢笑声。作者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过自己在城市寻到的一片菜园,传达了对生命归宿的思考。我深有同感。只有和土地打过交道的人,才能彻悟土地的力量。她养育着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同时养育着匍匐其上的村民。她不挑剔,不吝啬,不嘲笑。一代一代,大多数人,生于斯,长于斯,葬于斯。日月不老,辈辈接续。
无论有多么不舍,农耕文明为主体的时代终究是过去了。生活于城市的我们一面喝着星巴克,吃着西餐,一面在夜深人静之时,留恋着故土,思索着灵魂的归处。我们时常不自觉地伸出记忆的手,想抓住一片飘落的杨树叶,想录下盛夏里的一片蝉声,想抚摸风吹过时的麦浪,想趟过清澈见底的小河。这一切的一切,就像母亲永远为我们而开的大门,永远为我们铺好的床铺,等着我们归来。叶浅韵的生生系列是一口井,映照着每一个与乡村有关联的情节。她关照着乡村的当下,也思考着乡村的未来,同时将乡村之思延展到了城市之思。是呀,乡村是多少人离乡时带走的那口井,失意时念着它,得意时想着它。我想生生系列带给我们的,是根,是情。她期待着:当我们往回看的时候,并不颓唐;当我们向前走的时候,当坚定且有力量。
请允许我以此文致敬叶浅韵的《生生之门》,致敬彩云之南这片广博热土上的生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