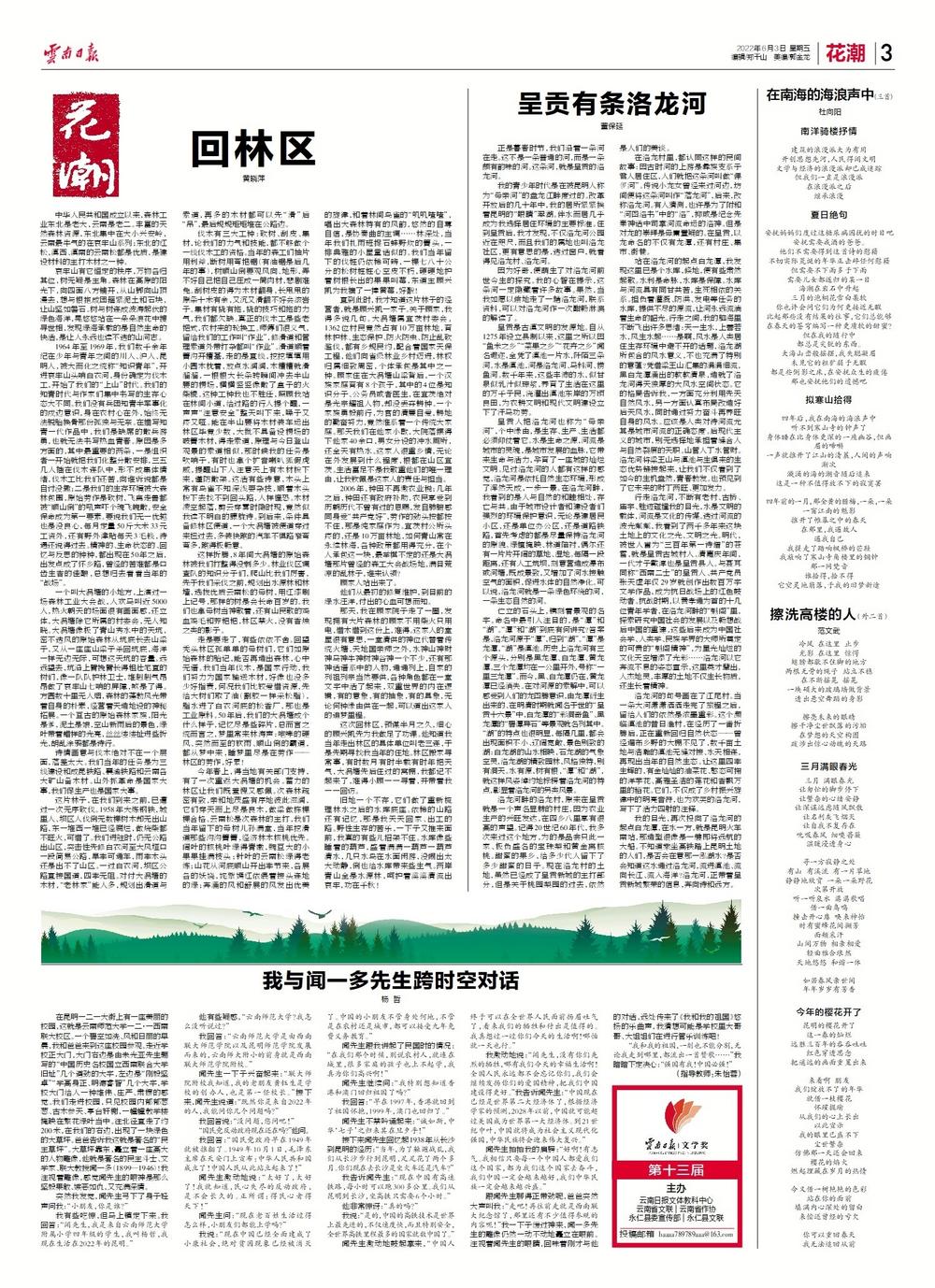黄晓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森林工业东北是老大,云南是老二。丰富的天然森林资源,东北集中在大小兴安岭,云南最牛气的在哀牢山系列;东北的红松,滇西、滇南的云南松都是优质,是建设材料的主打木材之一种。
哀牢山有它恒定的秩序,万物各归其位,树无疑是主角。森林在高原的阳光下,向四面八方铺开,从山脚向山顶漫去,想与根抱成团箍紧泥土和石块,让山坚如磐石。树与树连成波涛起伏的绿色海洋,晃悠悠站在一朵朵浪花中搜寻世相,发现绿海承载的是自然生命的快活,是让人永远也读不透的山河志。
1964年至1969年,我们数千余年纪在少年与青年之间的川人、沪人、昆明人,被大而化之统称“知识青年”,开进哀牢山头哨白衣河,身份确定为伐木工,开始了我们的“上山”时代。我们的知青时代与作家们集中书写的生存心态大不同。我们没有兵团知青半军事化的戍边意识,身在农村心在外,始终无法脱胎换骨那份孤独与无奈。在描写知青一代作品中,我们是缺席的散兵游勇,也就无法书写热血青春。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两条,一是组织者一开始就把我们化整分散安排,三五几人插在伐木连队中,形不成集体情绪,伐木工比我们还苦,向谁诉说都是自讨没趣;二是我们的生存环境被大森林包围,原始劳作是砍树,飞禽走兽都被“顺山倒”的吼声吓个魂飞魄散,安全保命成为第一要素。要说我们无一优越也是没良心,每月定量50斤大米33元工资外,还有野外津贴每天3毛钱,待遇还说得过去。精神的、生命状态的、回忆与反思的种种,都出现在50年之后,出发点成了怀乡路,曾经的苦难都是口齿生香的佳酿,总想归去看看当年的“战场”。
一个叫大涡塘的小地方,上演过一场森林工业大会战,人欢马叫近5000人,热火朝天的场面很有画面感,还立体,大涡塘除它所属的村委会,无人知晓。大涡塘像极了青山秀水中的天坑,密不透风的原始森林从坑底长去山梁子,又从一座座山梁子杀回坑底,海洋一样无边无际,可想这天坑的容量。远远望去,坑沿上臂挽臂长得粗壮笔直的树们,像一队队护林卫士,雄赳赳气昂昂做了哀牢山七哨的屏障,煞是了得。方圆数十里无人烟,森林的蓬勃风光带着自身的朴素,经营着天造地设的神秘拓展。一个亘古的原始森林家族,阳光是爹,泥土是娘,空山新雨后的景色,绿叶带着蜡样的光亮,丝丝缕缕扯进些折光,胡乱涂鸦都是诗行。
诗情画意与伐木绝对不在一个层面,落差太大。我们当年的任务是为三线建设和成昆铁路、襄渝铁路和云南各大矿山备木材。山外抓革命是国家大事,我们促生产也是国家大事。
这片林子,在我们到来之前,已遭过一次无序砍伐。1958年大炼钢铁,城里人、坝区人伐倒无数棵树木却无出山路,东一堆西一堆已经腐烂,做烧柴都不旺火,可惜了。我们进驻时,仍无公路出山区,突击性先修白衣河至大风垭口一段简易公路,旱季可通车,雨季木头还是出不了山区。一过白衣河,坝区公路直接国道,四季无阻。对付大涡塘的木材,“老林家”能人多,规划出滑道与索道,再多的木材都可以先“滑”后“吊”,最后规规矩矩堆在公路边。
伐木有三大工种:砍树、刮皮、集材,论我们的力气和技能,都不够做个一线伐木工的资格。当年的森工们抽片用利斧,断树用弯把锯(有油锯是后几年的事),树顺山倒要观风向、地形,弄不好自己把自己压成一筒肉材,悲剧难免。刮树皮的得为木材翻身,长甩甩的原条十米有余,又沉又滑翻不好会滚岩子。集材有撬有拖,撬的技巧和拖的力气,我们都欠缺。真正的伐木工是些老把式,农村来的轮换工。师傅们很义气,留给我们的工作叫“作业”,修滑道和管理索道外带打杂都叫“作业”。滑道顺着箐沟开槽基,走的是直线,挖挖填填用小圆木枕着,放点水润润,木槽槽就滑溜溜,一根根大长条转瞬间冲去半山腰的楞场,横横竖竖像散了盒子的火柴棍。这种工种我也不胜任,照顾我站在林间小道,给过路的行人提个醒,一声声“注意安全”整天叫下来,嗓子又疼又哑。能在半山腰将木材装车运出林区毕竟少数,大批不具备设楞场的破箐木材,得走索道,原理与今日登山观景的索道相似,那时候我的任务是吹哨子,有时也拿个扩音喇叭狐假虎威,提醒山下人注意天上有木材梭下来,谨防散架。这活有些诗意,木头上常有鸟雀不知深浅耍杂技,顺着木头梭下去找不到回头路,人样惶恐。木材凌空起落,剪云穿雾时隐时现,竟然似我读不明白的朦胧诗。到后来,条件具备修林区便道,一个大涡塘被便道穿过来扭过去,多装快跑的汽车不惧路窄弯弯多,跑得极畅意。
这样折腾,8年间大涡塘的原始森林被我们打整得没剩多少。林业伐区调查队的知识分子们,爬山比我们厉害,先于我们采伐之前,规划出水源林和林墙,选拔优质云南松的母树,用红漆刷上记号,那样的树是会长命百岁的。我们也拿母树当神敬着,还有山民敬的鸡血鸡毛和荞粑粑,林区禁火,没有香烛之类的影子。
走是要走了,有些依依不舍。回望秃头林区孤单单的母树们,它们如原始森林的胎记,能否再造出森林,心中无谱。我们当年伐木,是国家行动,我们努力为国家输送木材,好像也没多少好指责,何况我们比较爱惜资源,先给大树们取了油(割胶一样采松脂),脂水进了白衣河底的松香厂,那也是工业原料。50年后,我们的大涡塘成个什么样子,记忆尽是些碎片,总而言之统而言之,梦里常来林涛声:咆哮的硬风、突然而至的软雨、顺山倒的霸道,都从梦中来,睡梦里尽是在劳作——林区的劳作,好累!
今年春上,得当地有关部门支持,有了一次重返大涡塘的机会。蓄力的林区让我们既羞愧又感佩。次森林疏密有致,亲和地茂盛有序地彼此滋润,它们穿天而上尽是良木,做梁做栋棵棵合格。云南松是次森林的主打,我们当年留下的母树儿孙满堂,当年挖滑道那些沟沟箐箐,经济林木核桃优先。阔叶的核桃叶绿得青嫩,豌豆大的小果果挂满枝头;针叶的云南松绿得老练;山花从河底顺山开出季节来,各展各的妖娆,姹紫嫣红依偎着接头连地的绿;奔涌的风和舒展的风发出优美的旋律,和着林间鸟雀的“叽叽喳喳”,唱出大森林特有的风韵,悠然的自尊自信,是协奏曲的主调……林深处,当年我们扎雨班捉石蚌野炊的箐头,一排典雅的小屋童话似的。我们当年留下的伐桩仍依稀可辨,一棵七八十公分的松树桩桩心空皮不朽,硬硬地护着树根长出的果果叫莓,东道主顾兴凯为我摘了一捧黄莓,好酸!
直到此时,我才知道这片林子的经营者,就是顾兴凯一家子。关于顾家,我得多说几句。大涡塘属宜茨村委会,1362位村民竟然占有10万亩林地,育林护林、生态保护、防火防虫、防止乱砍滥伐,都有乡规民约,配合着国家天保工程,他们向省级林业乡村迈进,林权归属细致周密,个体承包是其中之一种。顾家住在大涡塘山梁背后,一个汉族家庭育有8个孩子,其中的4位是知识分子、公务员或者医生,在宜茨绝对是光宗耀祖人物,却没丢弃耕种。一个家族勇毅前行,为官的清廉自爱,耕地的勤奋努力,竟然维系着一个传统大家庭。那天我们在他家小歇,大院落摆得下他家40余口,男女分设的冲水厕所,还全天有热水。这家人很重乡情,无论在外发展到什么程度,根都在山区宜茨。生活富足不是我敬重他们的唯一理由,让我钦佩是这家人的责任与担当。
2006年,种田不再缴农业税;几年之后,种田还有政府补助,农民享受到历朝历代不曾有过的恩赐,发自肺腑感同身受“共产党好”,劳作的劲头按都按不住,那是纯家庭作为。宜茨村公所头疼的,还是10万亩林地,如何青山常在永续林海,各种政策都用得充分,在个人承包这一块,最举棋不定的还是大涡塘那片曾经的森工大会战场地,满目荒凉的乱林子,谁来认领?
顾家人站出来了。
他们从最初的修复维护,到目前的绿水汪洋,付出的心血可想而知。
那天,我在顾家院子走了一圈,发现拥有大片森林的顾家不用柴火只用电,惜木惜到这份上,难得。这家人的堂屋很有意思,一堂清供的神位代替着传统火塘,天地国亲师之外,水神山神财神马神牛神树神谷神一个不少,还有那神话谱系中的人物,通通列上,自家的列祖列宗当然要供,各种角色都在一堂文字中活了起来,双重世界的内在逻辑,有的意象,有的抽象,有的具象,无论何种缘由供在一起,可以道出这家人的追梦里程。
这次回林区,预谋半月之久,细心的顾兴凯先为我做足了功课。他知道我当年走出林区的具体单位叫老三连,于是先期寻找我当年的住地。林区搬家寻常事,有时数月有时半载有时年把天气,大涡塘先后住过的窝棚,我都记不起来了,难得小顾一一寻着,并带着我一一回访。
旧地一个不存,它们做了重新梳理林水之后的水库底座。依稀的山路还有记忆,那是我天天回家、出工的路。野性生存的苦乐,一下子又推来面前,我真的有些儿招架不住。水库像些睡着的葫芦,盛着满满一葫芦一葫芦清水,几只水鸟在水面闲游,没闹出太大动静,倒也给水库带来些生气。两岸青山全是水源林,呵护着溪溪清流出哀牢,功在千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