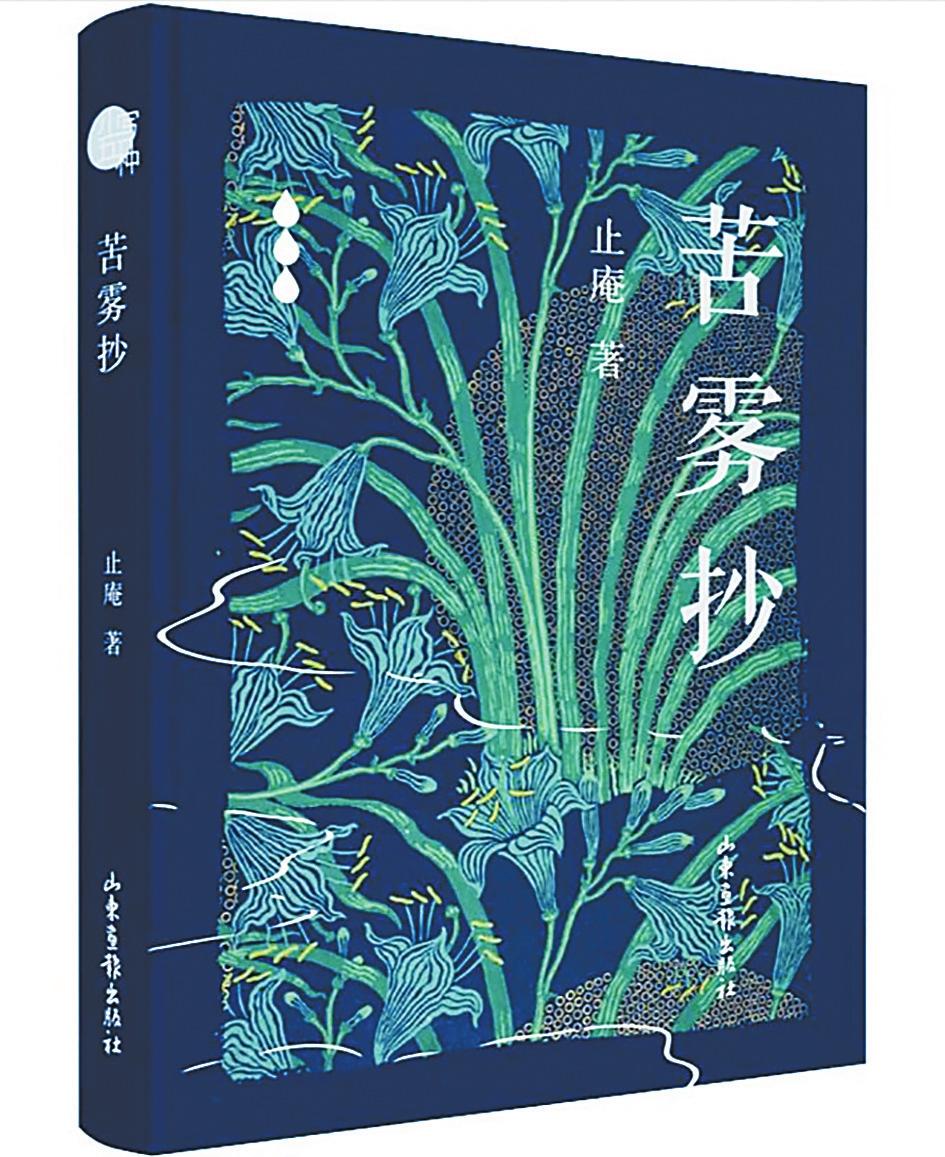朱航满
《苦雾抄》是止庵的第14本随笔集。他之前的13本集子,我都买来读过,且写过一篇《止庵文集识小》。当代作家中,止庵是我一直关注且喜欢的。我读他的第一本书是《六丑笔记》,记得是在南京图书馆的开架阅览室里借到的,当时只是觉得书名比较奇怪,写的内容也是我喜欢的方面。20多年过去了,我从他的一位读者,变成了与他相识的忘年交,他的书,也一直关注着。他曾送给我两本书,一本是朋友介绍我与他认识,在三联书店附近,赠我一册《如面谈》;另一本是我去他家中拜访,他赠我一册刚刚出版的《茶店说书》,还特别赠了一叶自印的藏书票。我后来编《中国随笔年选》,他是我遴选随笔最多的一位,总计大概有六七篇。有一年,他的著作《惜别》出版,我选了其中一章《母亲与读书》,有次在人民大学的一个新书讨论会上,他告知这篇并非全书最佳;由此他也多次推荐新作给我,其中便曾给我发来著作《画见》中的章节《画廊故事·女人(一到八)》,似乎那时候他还没有决定将这本书命名为《画见》。他还发来过一篇《我的父亲和他的诗》,收在这本《苦雾抄》中。
《苦雾抄》首篇为《春夜讲唐诗记》,刊发在2020年《文汇报》的“笔会”副刊上,我倾读之下,便是十分喜爱。当时新冠疫情肆虐,止庵在文章中说他宅在家中,晚饭后给家人讲解唐诗,每次选一家之作的四五首,或绝句,或律诗,或古风。《春夜讲唐诗记》共谈了5位,分别为王昌龄、贾岛、李贺、杜牧、陈陶,其中贾岛有两首诗,李贺有两首诗,每首诗谈一段,有点札记的意味,想来应该是从众多读诗笔记中摘选的。我非常喜欢他谈陈陶的《陇西行》,觉得意思很尖锐,似乎有暗讽的意味。他在文章中写道:“累累白骨散落在荒凉之地,‘春闺’也分布于天下各处。这正是此诗震撼人心的地方。”又写道:“哪些春闺梦是暖暖的、长长的,太阳升起犹迟迟未醒,同一个太阳也照耀着具具白骨,而这曾是一个个年轻、强壮、用‘貂锦’装扮得漂漂亮亮的将士。一具白骨,对应一位梦里人,一处春闺。”《苦雾抄》还有一篇随笔《我与树与花》,刊发在2021年《文汇报》的“笔会”副刊上,发表时还配了他家院子里一棵紫薇的彩色照片。这篇文章我也拟选在年选中,但这个选本的项目突然终止了。当时颇有一种特别的遗憾。
《春夜讲唐诗记》近于随笔,写自己的随感和读诗的札记,并不一定周全,但一定有自己独特的认识;《我与树与花》则应属于散文,叙写自己的故事,有着特别的生活体验。《在雪国重读〈雪国〉》,乃是他在日本寻访小说的故事发生地,并在此重读的札记,也是很有意思的。《关于李长声》《与友人谈游记书》等文章,大多属于这类随笔,写自己的对人与事的见识,多不流俗。而《我所见到的奈保尔》《夏目漱石的几处遗迹》《北京故事》《喝茶》等,则属于叙事散文了。《苦雾抄》中还有几篇,诸如《周作人与希腊神话》《周作人与汤尔和》《张爱玲文学的与众不同之处》等,接近于学术论文,写得十分周密,但文章娓娓道来,不觉得生硬。尤其是前两篇,乃是有新材料,亦有个人见识,写得抽丝剥茧,颇见功力。止庵的诸多文集,每个集子都会收录几篇谈周作人与张爱玲的文章,这是他下功夫最深的两位作家,也最能使文集显得有分量的地方。之前写张爱玲的文章,已经汇编成了一册《讲张文字》,但这两篇并没有收录。他谈周作人的文章,如果汇编成册,那一定是很厚的一本著作。
在《苦雾抄》中,也可见出止庵的写作范围,大体有三个方面,一是文学随笔,多介于文学评论与文学论文之间,诸如谈庄子、唐诗、周氏兄弟、张爱玲,以及他感兴趣的一些中外作家作品,后者大体以中国现代作家和西方现代经典作家为主;另一则是谈日本,上述《关于李长声》,谈的其实是“知日”这个问题,还有谈川端康成,以及他在日本参观作家故居的事情,这个爱好在他的日记体作品《游日记》中体现比较明显;还有一个则是谈北京,此书中收录的《我怎样写〈受命〉》《北京故事》《喝茶》《生火》《我与树与花》等,都与北京有关的话题,也都与他的长篇小说《受命》相关。止庵的长篇小说《受命》写的是20世纪80年代的北京故事,我很喜欢这部小说,说来很喜欢止庵在小说中营造的那种特别的氛围,读来很有种代入感。后来我想这与止庵的写作方式有关,他的小说写得也很像随笔,有些追求废名的小说《桃园》的意思。止庵还有一个爱好便是看电影和观画,前者似乎很少写过东西,记得只写过一组谈电影与文学原著的文章,收在他的随笔集《拾稗者》中;后者则有一种随笔集,分别为《画廊故事》和《画见》。
在《苦雾抄》中,还有一个很值得注意的地方。止庵在文章中数次阐述的一个观点,便是对于信息泛滥时代写作者的思考。在《关于李长声》中,他这样写道:“如今在互联网上,信息的更新较之过去迅速得多,信息的查询也便利得多。对于一位作者来说,写作到底因此变得容易了,还是困难了;应该多写,还是少写;有些内容需要写,还是不必再写,都是无法回避的问题。‘信息爆炸’之际,只有真正属于个人的声音才有可能不被淘汰。那种仅仅依仗语言优势的‘编译’,同样很容易被替代。”在《我怎样写〈画见〉》中,他亦写道:“从《画廊故事》到《画见》,差不多隔了20年,其间最大的改变是网络在我们的生活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从网上轻松地就能获取信息,譬如画家的生平逸事,美术史上的相关介绍之类,照搬这些东西放进书里——不妨称为‘代人百度体’——毫无意义,也毫无价值。或者要说,这样写也无妨,总归有人懒得去查。对此我更难以置信,连网都懒得上的人,怎么会有精力读你的书,而且还要花钱去买。所以,如果不写一己之见就根本没必要写书。”文章《与友人谈游记书》中,也表达了类似的意思。
其实,在止庵的上一本文集《风月好谈》的序言中,也有过类似的表达:“我刚开始写作时就想:世上已有那么多文章,为什么还要再写呢,一篇写完或多或少总要道出他人之所未道,或大或小总得消除某个疑问罢。到了互联网时代又增添了新的想法:网上可以轻易查到的东西,为什么还白费力气写成文章呢,有了Google或百度,我们应该写得更少才是。”由此,忽然想到止庵在文集《苦雾抄》的序言中所写的一段话:“距前一本《风月好谈》出版已过了5年多,区区十万字竟写了这么久,甚矣吾衰矣。”当时读这段文字的时候,印象很深。若仅仅以随笔写作为例,这5年时间,他写得确是少了。后来想想,这便是典型的止庵式的自谦,乃至傲气。因为在这5年时间里,他写了一本随笔集《画见》,又写了一部长篇小说《受命》,还整理出版了一册《游日记》,再加上这册随笔集《苦雾抄》,不算其他编订的作品,成绩也算是很不差了。待读了《苦雾抄》之后,觉得相比过去,他的写作内容更为丰富,类型更为多样,而态度也更为审慎和清醒,这倒是给包括我在内的当今写作者一个启发。这也可能是我持续关注止庵的一个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