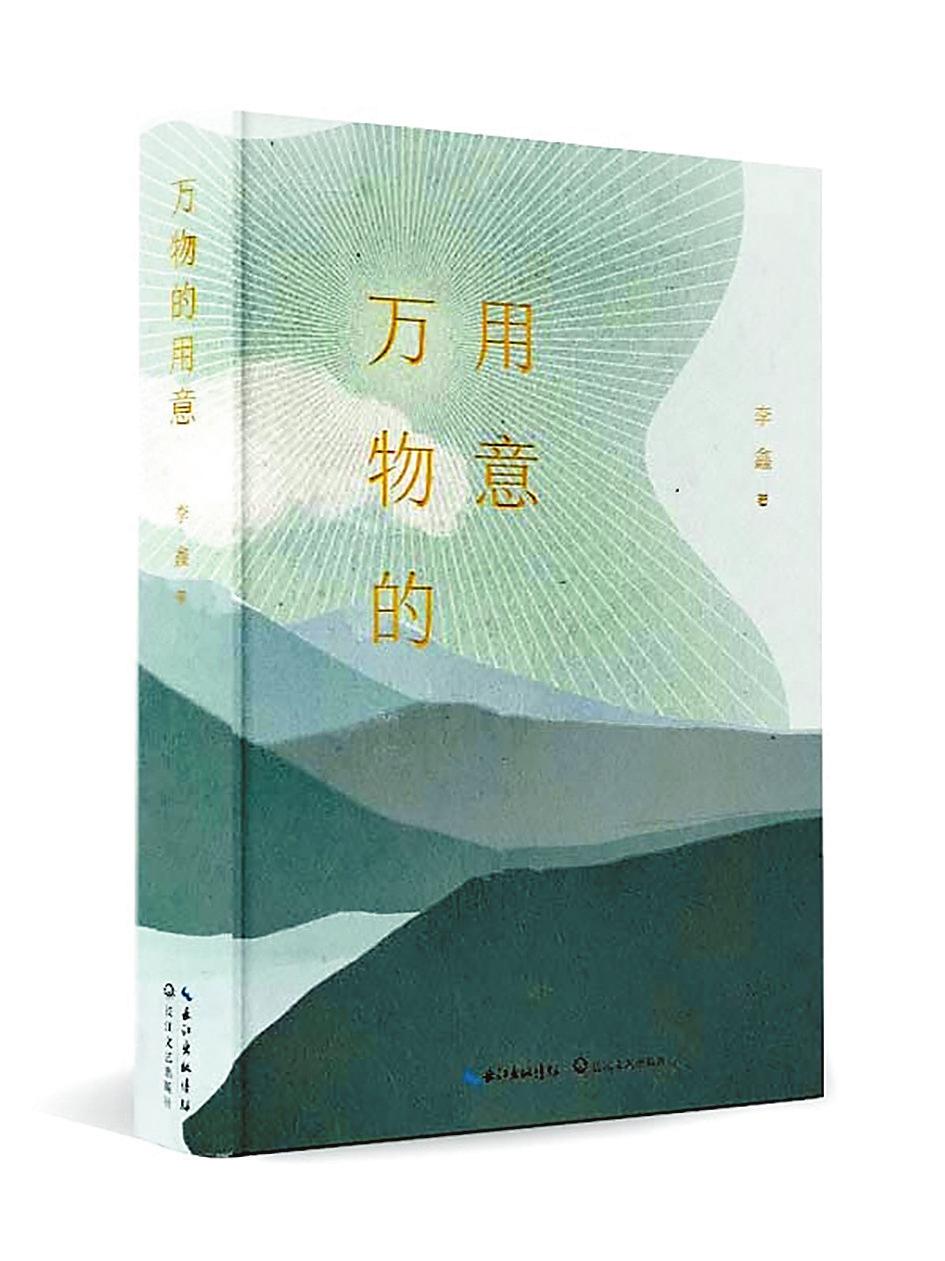童七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因为地貌特征不同,云南在城市化进程背后,一部分人的故土与乡梦依然存于乡村之中,因此,“乡土”作为诗歌景观和文化背景仍然存续于诗人的作品中。这些特点,在云南诗人李鑫的诗歌中体现得尤为典型。
李鑫出生于昭通农村,后来为谋生计离开家乡去广东发展,直到如今。和善于在诗歌中写人生经历的诗人不同,李鑫不太以“经历”入诗,他的诗歌中很少看到对社会生活、人生经历的描写,更多是个人片刻思索、对某种场景的短暂回望与观察。这样的写作特点,在他2022年8月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诗集《万物的用意》以及近来发表的组诗中都体现得很明显。
《万物的用意》是李鑫书写故土,回忆、回望那片土地时截取片段呈现的诗意。阅读这些诗歌让人不得不感慨,在生活方式已发生巨大改变的现代社会,“乡土”依然是促使诗人生发诗意的地方。《万物的用意》共5辑,分别是“太阳指针”“月亮记忆”“蝴蝶星辰”“山水雷音”和“暮色长河”。从题目取名可以看出,这些内容虽然看起来各自独立,实质上在意象书写和诗歌架构方面有着相似性。山水、秋风、月、蝴蝶等是诗集中常出现的意象。这些意象是诗人通过诗歌到达故土的钥匙,也是他在离开家乡的途中最常遇到的事物。
对于诗人李鑫来说,诗歌是技术与艺术的结合体。正如《枯萎的蛇》一诗所言——“你看我寂静的样子,像不像雨水中低垂的田野和山峰”——艺术传达的是他对这个世界的感受和欣赏,而技术则是他对这个世界的重新呈现。日常性是当代诗歌写作中常被提及的一个写作特性,日常性甚至已经成了生成当代诗歌的一个经典要素,但李鑫的诗语用传统的赋比兴手法反抗着日常性的铺陈。例如《空柿树》一诗,题名即是所写的内容,但是诗歌的主体内容却只有很少的部分直接写柿子树:“所有的灯盏都灭了/只剩下怀中从未点燃的那一盏,还有复活的机会”。空柿树是起兴缘由,而整首诗在后文的铺陈抒情中并没有再写柿子树的其他内容,而是把冬天的柿子树比喻成灯盏,后续行文则是从这个暗喻的灯盏铺展开去。又如《灯下》一诗,起始句仍然是与题名相关的内容:“一个人坐着,就是另一种天气/你看着桌子上的反光,正加速变凉”,后来的内容却是从这个场景开始延伸和铺展,无论是“古旧的集市”,还是“素不相识的面孔”,都朝着“此刻”的陌生走去。这些回忆中的事物支撑起了一个充满凉意的场景,这是属于李鑫诗歌的惯常生成路径。《星空》《风那么大》《夜空》等诗歌都是此类型的衍生。
在惯常的写作技法之外,李鑫诗歌中的亲情和爱情最为动人。写亲情的诗中对“祖母”和“母亲”的书写是他诗歌的常见主题。《手机屏幕上的雪山》从一张照片展开对祖母的怀念,“我看着我的祖母,在雪山的身体上/慢慢浮现”,这是描写“片刻”的典型代表;《窗台上有月光的凝视》写法与之相似,“想起风,想起风中摇摇晃晃的母亲/那么,这样一个想母亲的念头凝视过来”,这些“想起”维持了李鑫诗歌中高于现实的那部分质地,同时,一些诗句开始朝着“思”的内容走去。同样在这首诗中,想起母亲的脸,接下来的叙述是:“你看着凝视在缓缓起身,她开始沿着窗台走动,她成了我母亲的词语”。在这里,“凝视”作为一种动作,和凝视中的“母亲”合体,也可以看出李鑫在诗歌中对于想念的构筑。爱情主题在《馈赠》一诗中尤为突出,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从中多少可以窥见李鑫对于爱情的看法。“她私藏着春天奔向我/……她取出冰冷的火盆/枯萎的盘子……她说:这就是全部的爱情了”。这首诗歌不仅写出了爱情的美好,也写出了爱情中的苦涩、孤绝之感。同题的第二首写的是诗人与孩子之间的情感,这种情感和爱情一起组成了诗歌中与“父母/祖辈”不太一样的表达。写母亲和祖母的诗歌很大程度上是来自片段式的回忆,在诗意的剪辑和嫁接过程中营造出心理距离上的遥远之感,而诗人的爱情和与儿女之间的情感则多了一层更细腻的体贴:“和女儿还有许多游戏没有做完/我就要离开昆明了/她恨不得一天不睡觉/我恨不得时间焊死在一只时钟里”。
《万物的用意》在阅读中总让人产生一种“悬隔感”。这种悬隔感源于诗人绝大多数诗歌中对现实和诗意的处理方式。有着日常性和乡野气的组诗《声音》,诗歌的题名——“声音”“院中”“山顶”“山中”“湖边”“冬日”——就有着相似的悬隔感。《声音》一诗“发生”于山野之中,“群山宁静,山谷紧闭嘴巴/那些在山中徘徊的山雀/像孩子藏在嘴里的野果”;《山顶》:“多年后再次登上山顶的人/正想着半生的颓败,自我和解”“北风吹着身下的山河,几只寒鸦如铁”;《山中》:“山中无人,所有的声响此刻都只/说给我听”……“山”是诗意生发的重要意象、主要场所,除了“山”之形的刻画书写,李鑫还在“山”中凝聚了远离人世的静谧之美,这静谧之美的源头是李鑫向意象中注入的“悬隔感”。《声音》的山是宁静的,《山顶》的山没有声音,《山中》同样是没有人的山,安静的山是李鑫诗意寄居的地方,但是再往深处读会发现山的意象只是李鑫诗歌中的一个“噱头”,山的静谧和宁静才是李鑫诗歌真正的诗意生发地。
《声音》整组诗恰好是没有声音的。无论是以“山”为主要内容的诗还是其他诗歌,声音在李鑫诗歌里消失了。《声音》:“万物之声,正沉静地喷薄”;《某一刻》:“我想要更多的声音但没有”;《雪》:“我不懂雪,我看到的只是雪的沉默”;《院中》:“桂花树顶几个空鸟窝,在风里积累着宁静”……整组诗有“声音”的地方只有和女儿的对话:“孩子突然说:大地抱着这么多星星”“我想了半天对孩子说:你看这么多星星努力挤在一起/大地和我们,是不是多了美丽的反光”。对话其实也是在一个下雪的夜晚(安静的背景)下发生的,关于雪的对话其实不作为声音而存在,而只作为一种描述性的话语存在于诗歌当中。这首以“对话”开始又以“对话”结尾的诗歌中,语言失去了声音的属性,作为话语,它只为诗歌的整体意境服务。
以“静”作为切入点,在诗歌中可以看出李鑫的审美倾向。诗人喜静,在吵闹的生活之外,他的思想中永远有一个供自己生发诗意的僻静场所,这个场所又在每首诗的布局中带有随机性。《声音》中的场景是山谷;《院中》的场景即是乡里一个安静的小院;《湖边》就是安静的湖边。诗人在这些场景中构思一首诗歌,但是这种随机又只限于家乡的田野和山林。从内容选材上来说,李鑫的诗歌保有非常原生态的乡土特质。在乡土文化的背景中,诗人笔下的“静”有一部分继承自传统的“虚静”美学。
“虚静”是一种人生态度、写作状态和审美向度。文学创作中的虚静,需要写作者抛弃世俗陈杂的干扰转而进入一种“虚静”的写作状态,以这种审美的状态去观照万物,并从中找到诗意。这是文学中虚静的内涵之一。李鑫的诗歌在内容选材和诗意生发上显然与文学审美中的“虚静”内涵是吻合的,在众多的情绪状态中,他选中了“静”作为自己诗意的园地,被诗人选中的自然“万物”都在“静”的园地中铺展自己存在状态,这就让诗歌有了坚实的精神依托。
这种精神上的依托一方面很考验诗人的诗艺,另一方面就是诗歌造成“悬隔感”的精神来源。首先,“境”的“不实”会造成诗歌的悬空之感。李鑫的诗歌所选取的场景很多时候与他本人在生活中的存在状态是隔离的——作为工业文明中的社会运转之一环与诗歌中桃花源式的“静”中之境的隔离,甚至可以说,这个审美之境是诗人用力“构造”出来的,“构造”式的写作需要诗人更高的虚构能力。但在李鑫的诗歌中,他并没有执着于虚构本身,而是就一首诗的出发点,对经验进行剪辑和嫁接。同样的处理方式会造成诗歌的同质化,在李鑫的诗语中,这是较为明显的瑕疵。悬隔感的另一特点是某种分裂感。原生态的乡土特质和诗人的当下生活有着某种分裂感。虽然李鑫极力在诗歌中容纳诸如手机、电子照片等现代元素,但是很多时候这些带有现代科技感的事物并没有呈现出其本身的诗意,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李鑫仍然排斥着当下生活的现代性,这也是为什么山水事物一再成为生成诗歌要素的主要内容之一的原因。
而反观“宁静”何以成为诗歌中异常重要的特质,我想除了“宁静”是个体审美倾向之外,或许也是李鑫用以对抗庸常生活日常的方式之一。一位写作者,绝大多数时候长处即是他的短板。李鑫的悬隔感成就了他诗歌中几乎不闻烟火气的超然气息,这种超然气息中有诗性的静美,有时候也有短暂的思想式的漩涡,呈现出一定程度的丰富性。与此同时“悬隔”本身也带来了一些诗歌的悬空之感,场景的“不务实”会导致诗歌中一些情感不够真诚。而宁静的叙述让诗歌多了轻盈之态,但是与现实一旦有了过大的距离,就可以看出诗人的“偷懒”之处。对于生活在当代社会的个体,“勇于面对当下”仍然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课题,怎样把诗意从过去的乡土移植到当下的信息化社会也是每个写作者应该在诗歌中探索的内容。诗歌和文学是探索的艺术,也是勇于前进的艺术,因此,“怎么写”本身也是作者的人生态度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