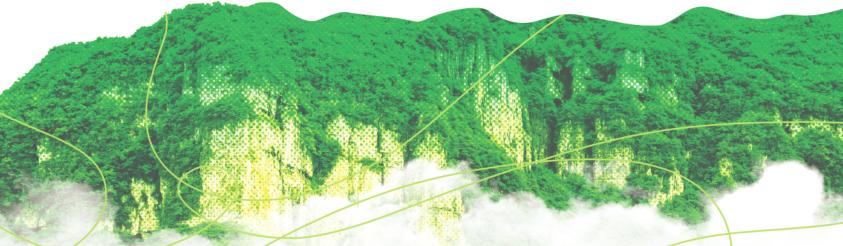曾春艳
“悬崖是世界的边缘,也是灵魂的深渊。”从这个层面来说,往返于石门关的人都是背着两面悬崖站在世界边缘的人,这悬崖既是具体数字建立起来的悬崖,更是想象建立起来的悬崖。无论是从西藏经石门关进入丙中洛的人,还是从云南经石门关进入察瓦龙的人,都是远走天涯的人,试图在倾斜的悬崖下寻找存在的边界:出关也好,入关也罢,这个“神仙也难通过的关口”都是通往异质化环境的必然通道,或者说都是试图通过地理空间的迁徙来重构个体记忆和生活意义的必然通道。而两侧光秃秃的峭壁,不仅是地理学层面断裂带的具象化,更是精神世界深渊凝视的抽象化:我们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面对着生命中注定的悬崖。
葡萄牙诗人佩索阿所面对的悬崖是里斯本的道拉多雷斯大街上徘徊的72个异名“他者”。智利诗人聂鲁达所面对的悬崖是拉丁美洲被割裂的历史。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所面对的悬崖是马孔多镇上那间用于自我囚禁的没有窗户的房间。日本作家三岛由纪夫所面对的悬崖是被烧毁的金阁寺。科幻作家刘慈欣面对的悬崖是把人类文明整体推向认知边缘的黑暗森林法则。悬崖不可回避,而如何面对悬崖是我们共同的困境。“我的命运是一座矗立的悬崖,写作是纵身一跃时抓住的藤蔓。”正如佩索阿在《想象一朵未来的玫瑰》中给出的答案:写作是面对悬崖的一种方式,但“真正的创作,始于我们承认自己永远身处悬崖这一侧,却依然向深渊投入词语的缆绳。”我一直试图在写作中寻找牵引我的那缕悬崖上的星光。
晨雾如撕碎的棉絮,一团团浮动在碧罗雪山和高黎贡山之间。左侧崖壁上盘踞着如蛛网般的植物根脉,未被植被覆盖的区域,是灰白色和黑色相间的岩石。灰白色是石块本来的颜色,黑色区域是死去的青苔赋予石块的颜色,那近乎垂直的角度让我脑海中浮现了记忆里的另一面悬崖:尼珠河大峡谷深处耸入云端的520米高的悬崖。右侧的崖壁上松萝悬垂下来,灰黄色的菌丝缠绕在一起。作为陆地上最早的拓荒者,以柔软之躯凿开坚硬的石床,靠着藻类和真菌这两种微脆生物,成为了悬崖上永远的寄生者。阳光如流淌的酥油般浸润着整个峡谷,怒江从阳光中流到阳光的阴影中。
从石门关向北翻越松塔雪山,就可以进入西藏察隅县察瓦龙乡的松塔村,这是完全意外的旅程。我看着黑色与土红色相间的崖壁上金属打造的“西藏”两个字,与相隔数米的“云南”并列而立,蓝色路标显示:“察瓦龙52km 察隅263km”。沿路标牌看向西藏方向,怒江滚滚而来,我竟然有些热泪盈眶:18岁想去的远方,此刻竟意外抵达了。我伸手抚摸着黑白相间的崖壁,久久不敢相信,我竟然真的抵达了西藏,那个曾长久活跃在我脑海中的远方。
当车驶过滇藏交界的界碑,往察隅方向继续行驶时。那恰洛峡谷两侧苍翠的针叶林逐渐取代了阔叶林的辖区,我被弥漫在空气中的松脂清香摄住。怒江在我的左侧奔腾不息,江面狭窄,水流湍急。江岸两侧的砂石被愤怒的江水淘洗后搁置在此,形成沿着流水蜿蜒的白色沙滩,像献给大地的哈达。逆着流水,驱车向前,不到10公里,我就被塌方拦住去路。这是此行遇到的第20次塌方。滚石如白色河流般从山脊滑落下来,大大小小堆叠在一起,截断了本就破烂不堪的土路,我再也不能向前了。怒江浑黄的浪涛还在身旁翻卷,可是我却不能再向前了。尽管我清楚地知道,即使没有滚石的阻隔,有限的时间也不允许我逆着流水回到它的“出处”。但我仍然感到遗憾,我想再往前走一走,哪怕只是一公里,也会减少一公里的遗憾。
和我一起被拦截在喜马拉雅山脉褶皱中的,还有一个穿红色骑行服的小姐姐,她和她的摩托车都贴满标签:“此生必骑丙察察”“此生必驾318”“西藏方向”“去远方”,张扬地把自己毕生追求的“别处”都展示给人群,这也是无数人渴望的“别处”啊。
当“进藏”或者说“去远方”成为一种潮流,当地理空间的跨越变成个人叙事的张扬时,我们不得不回头审视:远方是何方?是珠穆朗玛峰的雪线、斯米拉山口万古不变的冰川,或是库木塔格沙漠的群星?当我们凝视远方的时候我们又在凝视什么?是那个具体坐标所代表的经纬线,还是我们突破桎梏和边界所寻找的或者说所重塑的另一种生存可能?在米兰·昆德拉的《生活在别处》中,诗人雅罗米尔始终将生活寄托于诗歌的“别处”、爱情的“别处”,试图逃脱母亲的掌控和平庸的现实,但最终发现“别处”不过是虚构的镜像,他的一生也不过是从一个牢笼到另一个牢笼,始终困于意识深处编织的“远方幻觉”。
我们又何尝不是精神层面的雅罗米尔,从自己熟悉的地方到别人熟悉的地方去寻找所谓的“诗和远方”,说走就走或者预谋已久,当终于抵达远方时才发现:珠峰大本营凌晨三点的星空,和我少时爬上房顶看到是同一片星空,一样的璀璨、一样的辽阔、一样的令人惊喜,甚至正是因为少时抬头望向星空的那一刹震颤,在我心底种下了一颗星星,所以在珠峰大本营再次看到那么敞亮的星空,我才会如此感动。我们费尽心力所抵达的“向往之地”最终不过是被我们的想象异化的“重构之地”:远方所唤醒的不过是我们生命轴线所留下的某个瞬间的震颤,就像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中用玛德琳蛋糕重构的贡布雷。
碎石还在间歇性滚动,有些落入江中,在怒江滚滚涛浪的裹挟下奔向丙中洛,甚至奔向缅甸、奔向安达曼海,去构建高黎贡山深藏于海底的隐秘支脉。我不得不倒车艰难地退出这片区域。骑行进藏的小姐姐并不想止步于此,我看着她的红色骑行服,在后视镜中慢慢缩成一个红点。我不知道她最终是否坚定不移地抵达了她所期待的远方地标,但几个月后我抵达了被那次塌方阻拦而未抵达的终点。2024年10月初,我以另一种方式回到了怒江的“出处”。我隔着那曲河远远看着唐古拉山上的皑皑白雪,想象着雪水从吉热格帕峰汇聚而下,交融成了怒江最初的模样,被当地人以“那曲”命名,意为“黑色的河流”。河流碧波荡漾,从我眼前流过,流向云南,穿越他念他翁山与伯舒拉岭的夹击后,从海拔3000米的高原陡然倾泻至海拔1000米不到的谷地,在横断山脉的褶皱中劈出了中国最深的峡谷。此刻,我在此岸,唐古拉山在彼岸,我们在落日余晖中隔着万古冰川对望,我脑海中回荡的是海子在德令哈写下的诗句:“远方除了遥远一无所有。”我们注定无法抵达远方。远方从来不是一个具体的方位和坐标,而是每一次启程后的回眸,是“用他人的眼睛重新凝视自己的屋檐”的瞬间。但每一次奔赴远方的刹那,我们都在试图打破原有的边界和桎梏,寻找另一种生存的可能。就像此刻,那曲河的阻隔把唐古拉山变成了我生命中的另一个远方,但并不影响我接受来自在唐古拉山的抚慰,身旁的流水来自唐古拉山,从四面八方拥抱我的风也来自唐古拉山,我此刻对现实的感受和理解都是唐古拉山给予的。
秃鹫从上空划过,灰白色的羽毛飘落下来,长长的一根,靠近羽柄部的是乳白色绒毛,向另一端逐渐过渡为带着金属般坚硬质感的灰色羽枝。我看着这片雪域之上划过的那一抹弧线,忽然想到川西上空盘旋的成千上万只秃鹫群,它们在一瞬间突然而至,甚至看不清从何处来,然后又在转瞬间悄然离开,亦看不清飞往何处去,如幻影一般。也许此刻上空掠过的那一抹影子,也是当时从川西上空的秃鹫群投射下来的万分之一的影子,在寻找属于自己的另一个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