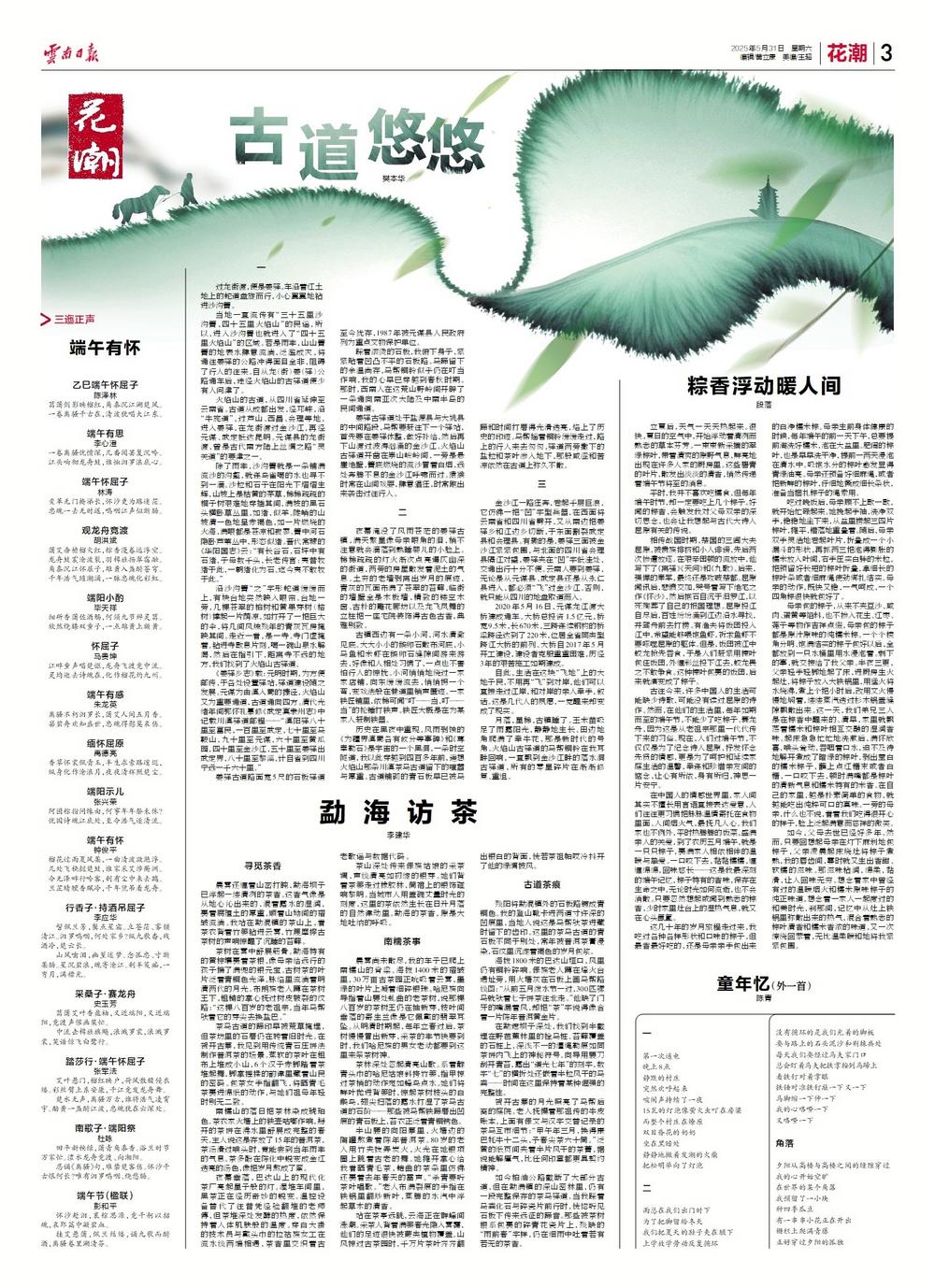樊本华
一
过龙街渡,便是姜驿。车沿着红土地上的蛇道盘旋而行,小心翼翼地钻进沙沟箐。
当地一直流传有“三十五里沙沟箐,四十五里火焰山”的民谣,所以,进入沙沟箐也就进入了“四十五里火焰山”的区域。若是雨季,山山箐箐的地表水肆意流淌,泛滥成灾,将通往姜驿的公路冲得面目全非,阻碍了行人的往来。自从龙(街)姜(驿)公路通车后,途经火焰山的古驿道便少有人问津了。
火焰山的古道,从四川省延伸至云南省。古道从成都出发,经邛崃,沿“牛旄道”,过芦山、西昌、会理等地,进入姜驿,在龙街渡过金沙江,再经元谋、武定抵达昆明。元谋县的龙街渡,曾是古代南方陆上丝绸之路“灵关道”的要津之一。
除了雨季,沙沟箐就是一条铺满流沙的沟壑,就连鸟雀喝的水也寻不到一滴。沙粒和石子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山坡上是枯黄的茅草,稀稀疏疏的桐子树艰难地穿插其间,满坡的黑石头横卧草丛里,如猪,似羊。陡峭的山坡清一色地呈赤褐色,如一片燃烧的火海,满眼都是苍凉和寂寥。箐中河石隐卧芦苇丛中,形态似猪。晋代常璩的《华阳国志》云:“有长谷石,石坪中有石猪,子母数千头,长老传言:夷昔牧猪于此,一朝猪化为石。迄今夷不敢牧于此。”
沿沙沟箐“之”字形蛇道缓缓而上,有块台地突然映入眼帘。台地一旁,几棵苍翠的柏树和黄果芽树(榕树)撑起一片荫凉,如打开了一把巨大的伞,将几间风烛残年的青灰瓦房掩映其间。走近一看,是一寺。寺门虚掩着。钻进寺歇息片刻,喝一碗山泉水解渴,然后在指引下,距离寺不远的地方,我们找到了火焰山古驿道。
《姜驿乡志》载:元明时期,为方便邮传,于各处设置驿站,驿道建设随之发展。元谋为由滇入蜀的捷径,火焰山又为重要通道,古道通向四方。清代光绪年间郭怀礼纂修《武定真隶州志》中记载川滇驿道邮程——“滇阳驿八十里至富民,一百里至武定,七十里至马鞍山,九十里至元谋,六十里至黄瓜园,四十里至金沙江,五十里至姜驿出武定界,八十里至黎溪,计自省到四川宁远一千六十里。”
姜驿古道路面宽5尺的石板驿道至今犹存,1987年被元谋县人民政府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踩着滚烫的石板,我俯下身子,紧紧贴着凹凸不平的石板路。马蹄留下的余温尚存,马帮铜铃似乎仍在叮当作响,我的心早已穿越到春秋时期。那时,西南人在这荒山野岭间开辟了一条通向南亚次大陆及中南半岛的民间通道。
姜驿古驿道处于盐源县与大姚县的中间路段,马帮要赶往下一个驿站,首先要在姜驿休整,做好补给,然后再下山渡过波涛汹涌的金沙江。火焰山古驿道开凿在崇山峻岭间,一旁是悬崖绝壁,箐底燃烧的流沙冒着白烟,远处奔腾不息的金沙江呼啸而过。猿猴时常在山间戏耍,肆意猖狂,时常跑出来袭击过往行人。
二
夜幕淹没了风雨苍茫的姜驿古镇,满天繁星像母亲眼角的泪,稍不注意就会滴落到熟睡婴儿的小脸上。稀稀疏疏的灯火渐次点亮逼仄幽深的街道,两旁的房屋散发着泥土的气息。土夯的老墙剥离出岁月的痕迹,青灰的瓦面布满了苍翠的苔藓,临街的墙壁全是木板墙,精致的镂空木窗、古朴的雕花廊坊以及龙飞凤舞的立柱把一座宅院装饰得古色古香,典雅别致。
古镇西边有一条小河,河水清澈见底。大大小小的鹅卵石散布河底,小马鱼和米虾在鹅卵石缝隙间游来游去,好像和人相处习惯了,一点也不害怕行人的惊扰。小河悄悄地绕过一家家店铺,向东缓缓流去,悄悄拐一个弯,变戏法般在巷道里销声匿迹。一家铁匠铺里,依稀可闻“叮——当,叮——当”的抡锤打铁声。铁匠大概是在为某家人赶制铁器。
历史在黑夜中重现,风雨剥蚀的《为疆界滇蜀各有攸分等事碑》和《尊奉勒石》是宇宙的一个黑洞,一条时空隧道,我以此穿越到四百多年前,遥想火焰山那条川滇茶马古道留下的喧嚣与厚重。古道铺砌的青石板早已被马蹄和时间打磨得光滑透亮,烙上了历史的印迹。马帮摇着铜铃缓缓走过,路上的行人来去匆匆,驿道两旁撒下的盐粒和茶叶渗入地下,那股咸涩和苦凉依然在古道上弥久不散。
三
金沙江一路狂奔,卷起千层巨浪,它仿佛一把“凹”字型兵器,在西面将云南省和四川省劈开,又从南边把姜驿乡和江边乡切断,于东面割裂武定县和会理县。有趣的是,姜驿三面被金沙江紧紧包围,与北面的四川省会理县隔江对望,姜驿夹在“凹”字低洼处,交通出行十分不便。云南人要到姜驿,无论是从元谋县、武定县还是从永仁县进入,都必须“飞”过金沙江。否则,就只能从四川的地盘取道而入。
2020年5月16日,元谋龙江渡大桥建成通车。大桥总投资1.5亿元,桥宽9.5米,长670米,三跨连续钢构的桥梁跨径达到了220米,位居全省同类型跨江大桥的前列。大桥自2017年5月开工建设,建设者克服重重困难,历经3年的艰苦施工如期建成。
自此,生活在这块“飞地”上的大地子民,不用再“飞”到对岸,他们可以直接走过江岸,和对岸的亲人牵手,叙话。这是几代人的夙愿,一觉醒来却变成了现实。
月落,星稀,古镇睡了。玉米苗吸足了雨露阳光,静静地生长。田边地角爬满了牵牛花,那是新时代的号角。火焰山古驿道的马帮铜铃在我耳畔回响,一直飘到金沙江畔的落水洞古驿道,所有的零星碎片在渐渐修复、重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