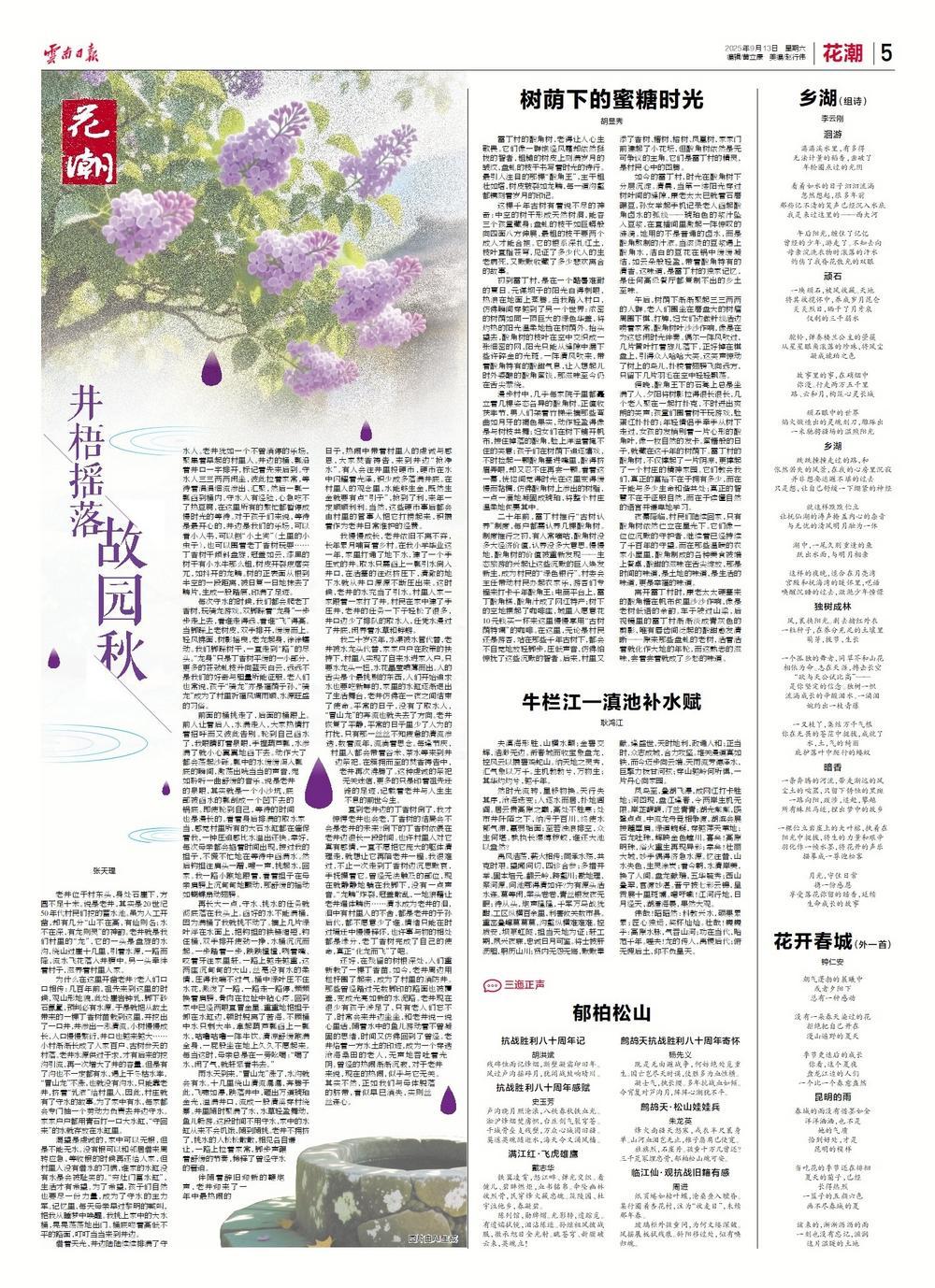张天理
老井位于村东头,身处石崖下,方圆不足十米。说是老井,其实是20世纪50年代村民们挖的蓄水池。虽为人工开凿,却有几分“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的神韵。老井就是我们村里的“龙”,它的一头是盘旋的水沟,绕山过崖十几里,引着水源,一路而降,流水飞花落入井腹中。另一头牵绊着村子,滋养着村里人家。
为什么在这里开凿老井?老人们口口相传:几百年前,祖先来到这里的时候,观山形地貌,此处崖岩钟乳,脚下砂石氤氲,预判必有水源。于是就把从故土带来的一棵丁香树苗栽到这里,并挖出了一口井,井渗出一泓清流。小树慢慢成长,人口慢慢繁衍,井口也越来越大……小村渐渐长成了人家百户、古树参天的村落。老井水源供过于求,才有后来的挖沟引流,再一次增大了井的容量。但是有了沟也不一定都有水,遇上干冬枯水季,“冒山龙”不涨,也就没有沟水,只能靠老井,挤着“乳液”给村里人。因此,村庄就有了守水的故事。为了家中有水,每家都会专门抽一个劳动力负责去井边守水。家家户户都用青石打一口大水缸,“守回来”的水就存放在水缸里。
渴望是虔诚的,家中可以无粮,但是不能无水。没有粮可以和邻居借来周转应急,等收粮的时候再还给人家,但村里人没有借水的习惯,谁家的水缸没有水是会被耻笑的。“穷灶门富水缸”,生活才有希望。为了希望,孩子们自然也要尽一份力量,成为了守水的主力军。记忆里,每天母亲早过黎明的喊叫,把我从睡梦中唤醒。我挑上家中的大水桶,晃晃荡荡地出门。桶底吻着高低不平的路面,叮叮当当来到井边。
借着天光,井边陆陆续续排满了守水人。老井犹如一个不曾消停的乐场,聚集着早起的村里人。井边的桶、瓢沿着井口一字排开,标记着先来后到。守水人三三两两闲坐,彼此拉着家常,等待着涓涓细流渗出、汇聚,然后一瓢一瓢舀到桶内。守水人有经验,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在这里所有的繁忙都暂停成慢时光的等待。对于孩子们来说,等待是最开心的,井边是我们的乐场,可以看小人书,可以刨“小土狗”(土里的小虫子),也可以围着老丁香树玩耍……丁香树干倾斜盘旋,冠盖如云,漆黑的树干有小水牛那么粗,树皮开裂疙瘩突兀,如抖开的龙鳞。树的正表面从根到半空的一段距离,被日复一日地抹去了鳞片,生成一股踏痕,印满了足迹。
每次守水的时候,我们都会爬老丁香树,玩骑龙游戏。双脚踩着“龙身”一步步走上去,看谁走得远、看谁“飞”得高。当脚踩上老树皮,双手排开,缓缓而上。轻风拂面,树影摇曳,老龙起身,徐徐蠕动。我们脚踩树干,一直走到“路”的尽头。“龙身”只是丁香树平缓的一小部分,更多的苍劲虬枝升向蓝天白云,远远不是我们的好奇与胆量所能征服。老人们也常说,孩子“骑龙”亦是福荫子孙,“骑龙”成为了村里祈福风调雨顺、水源旺盛的习俗。
前面的桶挑走了,后面的桶跟上。前人让着后人,水满走人,大家热情打着招呼而又彼此告别。轮到自己舀水了,我眼睛盯着泉眼,手捏葫芦瓢,水渗满了就小心翼翼地舀下去。动作大了都会荡起沙砾。瓢中的水缓缓泻入瓢底的瞬间,激荡出咣当当的声音,宛如聆听一曲舒缓的音乐。说是老井的泉眼,其实就是一个小沙坑,底部被舀水的瓢刮成一个凹下去的锅底。即使轮到自己,等待的时间也是漫长的。看着身后排满的取水家当,感觉村里所有的大石水缸都在催促着我,一种压迫感比水溢出还快。幸好,每次母亲都会掐着时间出现,接过我的担子,不慌不忙地在等待中舀满水。然后钩担往肩头一蹭,嗖一声,挑起水,回家。我一路小跑地跟着,看着担子在母亲肩膀上沉甸甸地颤动,那舒缓的摇动如蝴蝶扇动翅膀。
再长大一点,守水、挑水的任务就彻底落在我头上。舀好的水不能满桶,因为满桶了我就挑不动了。摘上几片绿叶浮在水面上,把钩担的铁链缩短,钩住桶,双手排开使劲一挣,水桶沉沉而起。一步踏着一步,跌跌撞撞,咧着嘴、咬着牙往家里赶。一路上越走越重,这两座沉甸甸的大山,丝毫没有水的柔情,压得我喘不过气。桶中绿叶压不住水花,溅泼了一路,一路走一路停,频频换着肩膀,骨肉在拉扯中钻心疼。回到家中已经两眼直冒金星。重重地把担子卸在水缸边,顿时脱离了苦海。不顾桶中水只剩大半,拿起葫芦瓢舀上一瓢水,咕噜咕噜一阵牛饮。清凉舒缓跑满全身,一屁股坐在地上久久不愿起来。每当这时,母亲总是在一旁吆喝:“喝了水,闲了气,就赶紧看书去。”
雨水天到来,“冒山龙”涨了,水沟就会有水。十几里绕山清流潺潺,奔腾于此,飞啸如瀑,跌落井中,砸出万道琥珀金光,溢满井口,流成一股清溪穿村绕寨。井里随时聚满了水,水草轻盈舞动,鱼儿畅游。这段时间不用守水,家中的水缸从来不会饥饿,随到随挑。老井不拥挤了,挑水的人松松散散,相见各自谦让,一路上拉着家常,脚步声碾着舒缓的节奏,稀释了曾经守水的窘迫。
伴随着辞旧迎新的鞭炮声,老井迎来了一年中最热闹的日子,热闹中带着村里人的虔诚与感恩,大家焚香祷告,来到井边“抢净水”。有人会往井里投硬币,硬币在水中闪耀着光泽,积少成多落满井底。在村里人的观念里,水能够生金,既然生金就要有点“引子”,抢到了利,来年一定顺顺利利。当然,这些硬币事后都会由村里的管事人把它打捞起来,积攒着作为老井日常维护的经费。
我慢慢成长,老井依旧不离不弃,长年累月哺育着乡村。在我小学毕业这一年,家里打通了地下水,建了一个手压式的井。取水只需舀上一瓢引水倒入井口,在活塞的往返挤压下,清澈的地下水就从井口源源不断压出来。这时候,老井的水充当了引水。村里人家一家跟着一家打了井。村民在家中建了手压井,老井的任务一下子轻松了很多,井口边少了排队的取水人,任凭水漫过了井底,闲养着水草和蜉蝣。
我二十岁这年,水渠被水管代替,老井被水龙头代替,家家户户在政策的扶持下,村里人实现了自来水进家入户。只要水龙头一扭,水花晶莹喷薄而出。人的舌尖是个最挑剔的东西,人们开始追求水也要吃新鲜的,家里的水缸逐渐退出了生活舞台,老井仿佛在一夜之间结束了使命。平常的日子,没有了取水人,“冒山龙”的奔流也就失去了方向。老井恢复了平静,平常的日子里少了人为的打扰,只有那一丝丝不知疲惫的清流渗透,数着流年,流淌着思念。每逢节庆,村里人都会带着谷米、茶水等来到井边祭祀。在簇拥而至的焚香祷告中,老井再次沸腾了。这种虔诚的祭祀无关迷信,更多的只是印着祖先迁徙的足迹,记载着老井与人生生不息的前世今生。
直到老井边的丁香树倒了,我才惊愕老井也会老,丁香树的结局会不会是老井的未来?倒下的丁香树依偎在老井边很长一段时间。也许村里人对它真有感情,一直不愿把它庞大的躯体清理走,就想让它再陪老井一程。我很难过,不止一次走到丁香树边沉思默哀,手抚摸着它。曾经无法触及的部位,现在就静静地躺在我脚下,没有一点声音。“龙鳞”炸裂,冠盖散乱,一地狼藉让老井遍体鳞伤……清水成为老井的泪,泪中有村里人的不舍,都是老井的子孙后代,都不愿意少了谁。情绪只能在时过境迁中慢慢释怀,也许事与物的相处都是缘分,老丁香树完成了自己的使命,真正“化龙而飞”了吧。
还好,在残留的树根深处,人们重新栽了一棵丁香苗。如今,老井周边用栏杆围了起来,成为了村里的消防井。那些曾经踏过无数脚印的路面也被覆盖,变成光亮如新的水泥路。老井现在很少有孩子涉足了,只有老人们忘不了,时常会来井边坐坐,和老井说一说心里话,随着水中的鱼儿游动着不曾凝固的思绪,时间又仿佛回到了曾经。老井烙着一方水土的印迹,成为一个穿透沧海桑田的老人,无声地吞吐着光阴。曾经的热闹渐渐沉寂,对于老井来说,现在的热闹,似乎与它无关。其实不然,正如我们与母体脱落的脐带,看似早已消失,实则丝丝连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