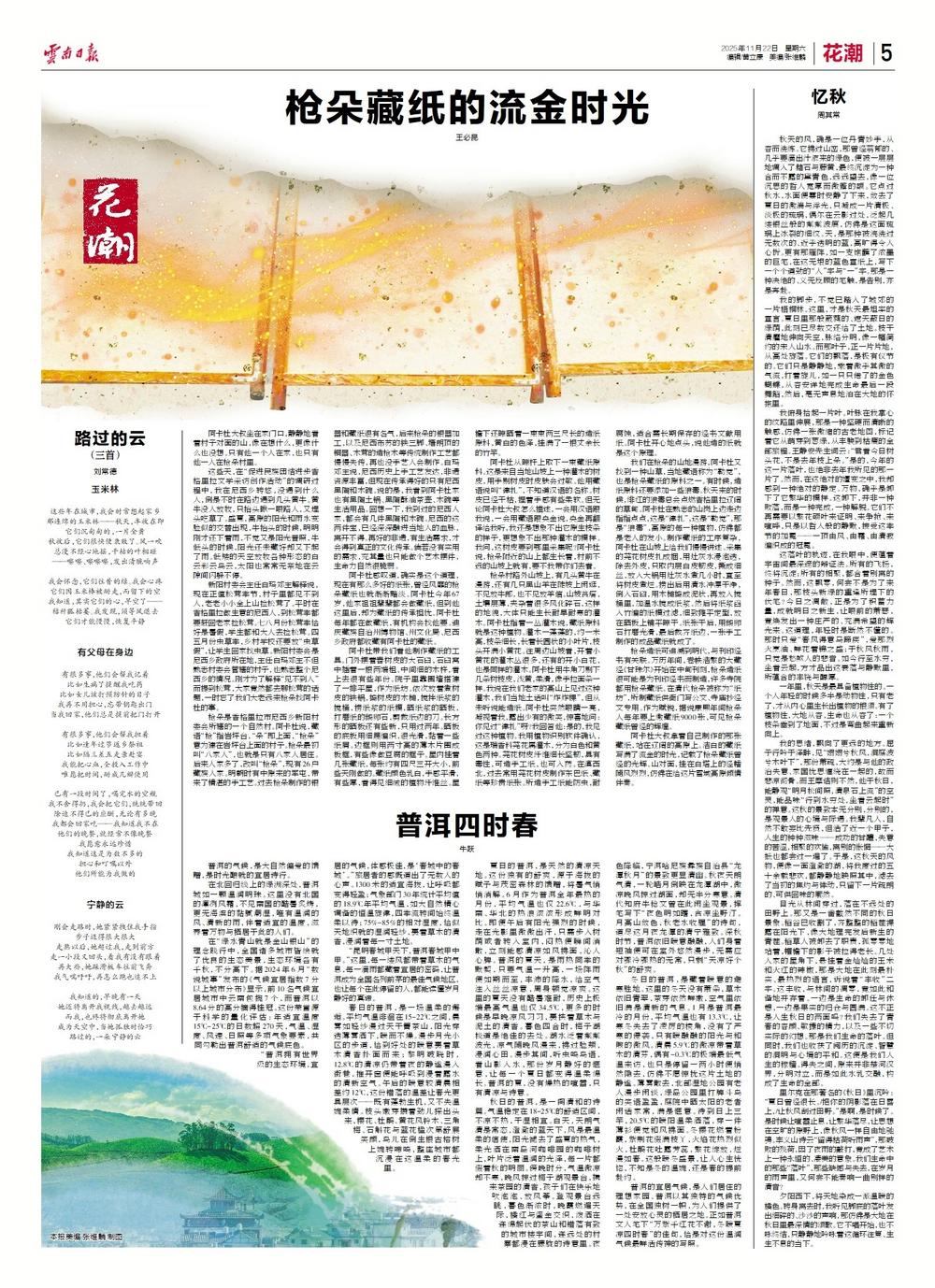周其常
秋天的风,确是一位丹青妙手,从容而洗练。它拂过山峦,那曾经蓊郁的、几乎要滴出汁液来的绿色,便被一层层地调入了赭石与藤黄,最终沉淀为一种含而不露的黛青色,远远望去,像一位沉思的哲人宽厚而微蹙的额。它点过秋水,水面便霎时安静了下来,敛去了夏日的激湍与浮光,只凝成一片清极、淡极的琉璃,偶尔在云影过处,泛起几缕银丝般的粼粼波痕,仿佛是这面琉璃上冰裂的细纹。天,是那种被浣洗过无数次的、近乎透明的蓝,高旷得令人心折。更有那雁阵,如一支饱蘸了浓墨的巨笔,在这无垠的蓝色宣纸上,写下一个个遒劲的“人”字与“一”字。那是一种决绝的、义无反顾的笔触,是告别,亦是奔赴。
我的脚步,不觉已踏入了城郊的一片梧桐林。这里,才是秋天最坦率的宣言。夏日里那般葳蕤的、遮天蔽日的绿荫,此刻已尽数交还给了土地。枝干清癯地伸向天空,脉络分明,像一幅简约的宋人山水。而那叶子,正一片片地,从高处旋落。它们的飘落,是极有仪节的。它们只是静静地,乘着微乎其微的气流,打着旋儿,如一只只倦了的金色蝴蝶,从容安详地完成生命最后一段舞蹈,然后,毫无声息地泊在大地的怀抱里。
我俯身拾起一片叶。叶脉在我掌心的纹路里伸展,那是一种坚硬而清晰的触感,仿佛一张微缩的古老地图,标记着它从萌芽到葱绿,从丰腴到枯瘦的全部旅程。王静安先生词云:“君看今日树头花,不是去年枝上朵。”是的,今年的这一片落叶,也绝非去年我所见的那一片了。然而,在这绝对的嬗变之中,我却感到一种绝对的静定。万物,确乎是卸下了它繁华的模样。这卸下,并非一种败落,而是一种完成,一种解脱。它们不再需要以繁花硕叶来证明、来争抢、来喧哗,只是以哲人般的静默,接受这季节的加冕——一顶由风、由霜、由清寂编织成的冠冕。
这落叶的轨迹,在我眼中,便蕴着宇宙间最深邃的辩证法。所有的飞扬,终将沉淀;所有的相聚,都含着别离的种子。然而,这飘零,何尝不是为了来年春日,那枝头新绿的重逢所埋下的伏笔?今日之凋敝,正是为了积蓄力量,成就明日之新生,让眼前的萧瑟,竟焕发出一种庄严的、充满希望的辉光来。这道理,年轻时是断然不懂的。那时只爱“春风得意马蹄疾”,爱那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之盛;于秋风秋雨,只觉是愁煞人的悲音。如今行至水穷,坐看云起,方才品出这衰落与静默里,所蕴含的丰饶与醇厚。
一年里,秋天是最具备植物性的。一个人年轻的时候多半是动物性,只有老了,才从内心里生长出植物的根须。有了植物性,大地从容,生命也从容了:一个枝条垂到了地面,不过是弯曲起来重新向上。
我的思绪,飘向了更远的地方。屈子行吟于泽畔,见“嫋嫋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那份萧疏,大约是与他的政治失意、家国忧思缠绕在一起的,故而悲凉彻骨。而王摩诘则不然,他于秋日,能静观“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空灵,能品味“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禅意。这秋的景致本无分别,分别的,是观景人的心境与际遇。我辈凡人,自然不敢妄比先贤,但活了近一个甲子,人生的种种滋味——成功的甘醴,失意的苦涩,相聚的欢愉,离别的怅惘——大抵也都尝过一遍了。于是,这秋天的风物,便像一面澄澈的湖,将我度过的五十余载悲欢,都静静地映照其中,滤去了当初的焦灼与悸动,只留下一片疏朗的、可供回味的廓然。
目光从林间穿过,落在不远处的田野上。那又是一番截然不同的秋日景象。稻谷已收割了,齐整整的稻茬裸露在阳光下,像大地理完发后新生的青茬。稻草人被卸去了职责,孤零零地站着,帽檐下的影子被拉得老长。几处人家的屋角下,悬挂着金灿灿的玉米和火红的辣椒,那是大地在此刻最朴实、最热烈的语言,诉说着“丰收”二字。这丰收,与林间的凋零,竟如此和谐地并存着。一边是生命的卸任与休憩,一边是果实的归仓与圆满。这不正是人生秋日的两面吗?我们失去了青春的容颜、敏捷的精力,以及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那是我们生命的落叶。但同时,我们也收获了阅历的沉淀、智慧的洞明与心境的平和。这便是我们人生的稼穑。得失之间,原来并非楚河汉界,分明对立,而是如此水乳交融,构成了生命的全部。
里尔克在那著名的《秋日》里沉吟:“夏日曾经很长。/把你的阴影落在日晷上,/让秋风刮过田野。”是啊,是时候了。是时候让喧嚣止息,让繁华落尽,让思想在空旷的原野上,像秋风一样自由地驰骋。李义山诗云“留得枯荷听雨声”,那破败的残荷,因了夜雨的敲打,竟成了艺术上一种永恒的、凄美的意象。我们生命中的那些“落叶”,那些缺憾与失去,在岁月的雨声里,又何尝不能奏响一曲别样的清音?
夕阳西下,将天地染成一派温暖的橘色。转身离去时,我听见脚底的落叶发出细碎的、沙沙的声响,那仿佛是大地在秋日里最深情的颂歌。它不唱开始,也不咏终结,只静静地吟咏着这循环往复、生生不息的当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