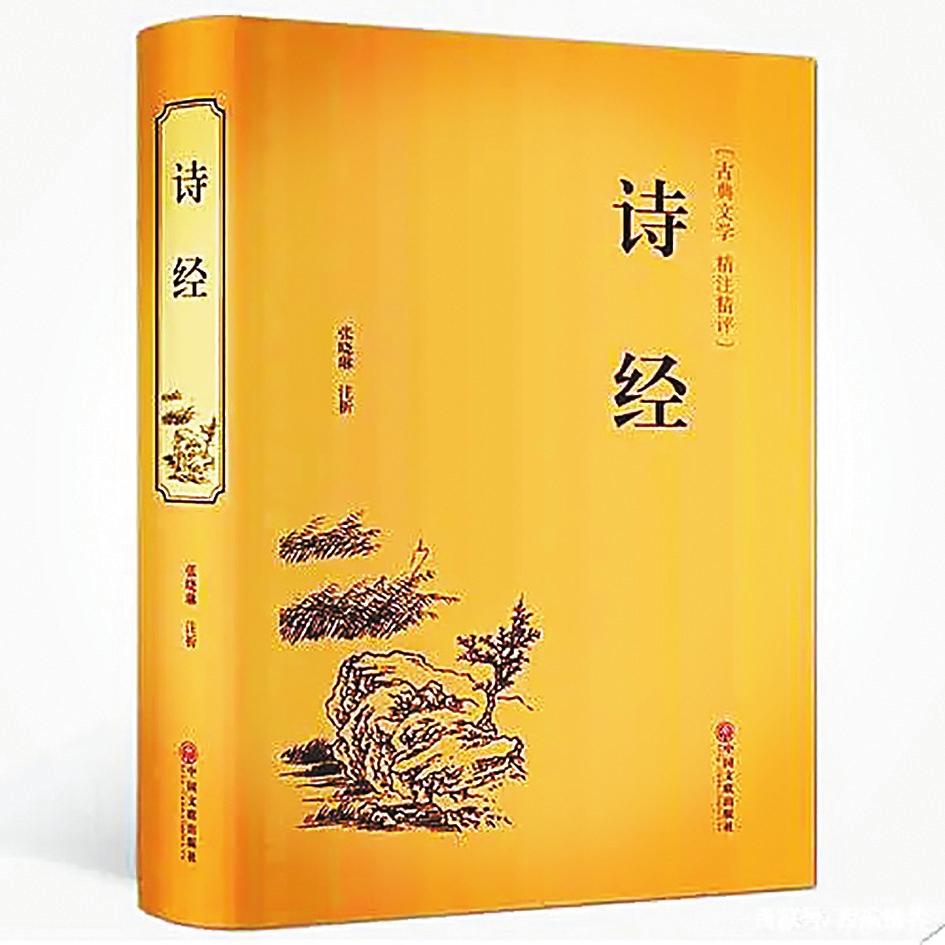苗连贵
原始劳动歌谣,口耳相传下来的不多,有文字记载的更其寥寥,但仅就散见于先秦典籍中零星的篇什看,大多铿锵有力,意气昂扬,催人奋发。其中最为后世称道的,大约当属《弹歌》(载《吴越春秋》):“断竹,续竹,/飞土,逐宍(古‘肉’字,代指禽、兽)。”
“断竹”,砍伐并截取竹子;“续竹”,是用韧性的藤葛或竹索做弦,制成弹弓,强劲有力;“飞土”,把泥做成弹丸,装在竹箭上,干了后坚硬异常,这样才能击伤猎物;“逐宍”,这样的弓箭不一定能“一‘箭’封喉”,猎物负伤而逃,这就要追逐了。八字短歌,流露出原始人对自己学会制造猎具的自豪感以及追逐并获得猎物的喜悦心情。
《蜡辞》(载《礼记》)也写得简短而有力:“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土,从哪里来的返回到哪里去;水,回到山谷中;害虫不要猖獗;草木,回到沼泽地带生长。大水泛滥,土地淹没,虫害猖獗,草木荒疏。这看似“咒语”,但态度坚决,声势凌厉,命令似语气,表现了先民改造自然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
与此相类的,还有一首《神北行》(载《山海经》):“神,北行!/先除水道,/决通沟渎!”“神”指旱神魃,驱逐它,回到它的原地北方,不许在此肆虐,使水道和沟渠畅通。这首歌,与祈求式的祭辞相比,更显出先民通过劳动征服自然的积极性及同艰苦的自然环境斗争的强烈意愿。
《易经》中还有这样的一首:“女承筐,无实;/士刲羊,无血。”男的看似宰羊,但不见血;女的将羊毛装筐,但没有重量。这首歌,大约是男女边劳动,边相互戏谑时对唱的,有情有景,表现出劳动中的嬉闹之态。
到了春秋,《诗经》记载的劳动诗歌就多了。原先以为,上古洪荒,生产力低下,以为那时生民劳作不知怎样受苦受难呢!近读(自然以前也读)《诗经》,读到有关劳动的篇章,发现全然不是“想当然”那么回事,诗里描绘的劳动情状不惟不苦,反而轻松愉悦,极具生活情味。如《魏风·十亩之间》:“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行与子还兮。//十亩之外兮,/桑者泄泄兮,/行与子逝兮。”“十亩”指桑园的大小,约数;“桑者”,采桑女;“闲闲”,采完桑,歇息时的轻松状;“泄泄”,同义。这是一首采桑的歌:在茂密的桑园里,采桑女辛勤地采摘,桑叶采得满筐满篓,该回家了,于是背起筐篓,结伴同行,一路笑语喧哗,表现了桑园里的和乐气氛和劳动后的欢快心情。
我特别喜欢《诗经》中的《周南·芣苢》,这是一首女子采摘车前子草的乐歌。余冠英先生将之译成白话,十分精妙,尽显民歌风味:“车前子儿采呀采,采呀快快采起来。/车前子儿采呀采,采呀采到手中来。/车前子儿采呀采,一颗一颗拣起来。/车前子儿采呀采,一把一把捋下来。/车前子儿采呀采,手提衣襟兜起来。/车前子儿采呀采,掖起了衣襟兜回来。”这首小诗章节回环复沓,通过反复咏唱,我们仿佛看到三五成群的女子在山坡旷野劳动的身形,听到她们的歌声,感受到她们采摘时的欢乐心情。
如果说《芣苢》是一首浸染着田野风的抒情小调,《大雅·緜》则是一首气势磅礴的创业者之歌。《緜》记载周人为了生存和发展,进行的一次全国性的大迁徙,开疆辟土,建设家园,是一首带有史诗性质的古歌。诗共四章,其中第四章直接写他们到了新地,整田筑室的劳动场景。上学时,老师褚斌杰先生把它译成白话:“装土运泥响陾陾,投土入板响轰轰。/捣土打墙登登登,削墙拍打砰砰砰。/百堵高墙平地起,劳动歌声胜鼓声。”如此艰辛的劳动却看不到先民们的苦楚,有的只是高扬的劳动热情和创业的自豪感。这使我想起在“战天斗地”年代,那种出大力、流大汗、以苦为乐的情怀。劳动并不苦,劳动换来成果,劳动让人憧憬美好幸福的明天。
在《诗经》中,有关劳动的诗几乎都写得很“乐呵”,即如《伐檀》《七月》,也是“以劳动为起兴”表现对不劳而获的贵族老爷的不满、讽刺甚至反抗,劳动者对劳动本身是并无怨尤的。
劳动创造了人,劳动是人的自身需要,所以劳动起来多不觉苦(但在鞭子和棍棒下的劳动除外,那是苦役)。即使劳动的过程艰辛万分,人们也会从中找乐,使之变得轻松愉快起来。我记得20世纪的劳动工地,譬如修路或筑坝,常见人们唱“夯歌”,边打夯边唱,一人起头,众人齐和,歌词即兴发挥,出口成章,合辙押韵,风趣调侃。夯歌使人们在高强度的劳动条件下心情放松,精神饱满,感到有使不完的劲。这种情状,其实在远古社会就已出现,《淮南子·道应训》记载:“今夫举大木者,前呼‘邪许’,后亦应之,此举重劝力之歌也。”“邪许”就是人们集体劳动时的一唱一和,藉以调整动作,减轻疲劳,加强工作效率的呼声。“邪许”(鲁迅称之为“杭育”)之属、《诗经》里的劳动歌声,以及那个年代随口创作的各种“夯歌”,也就是所谓的诗了,劳动是诗歌创作的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