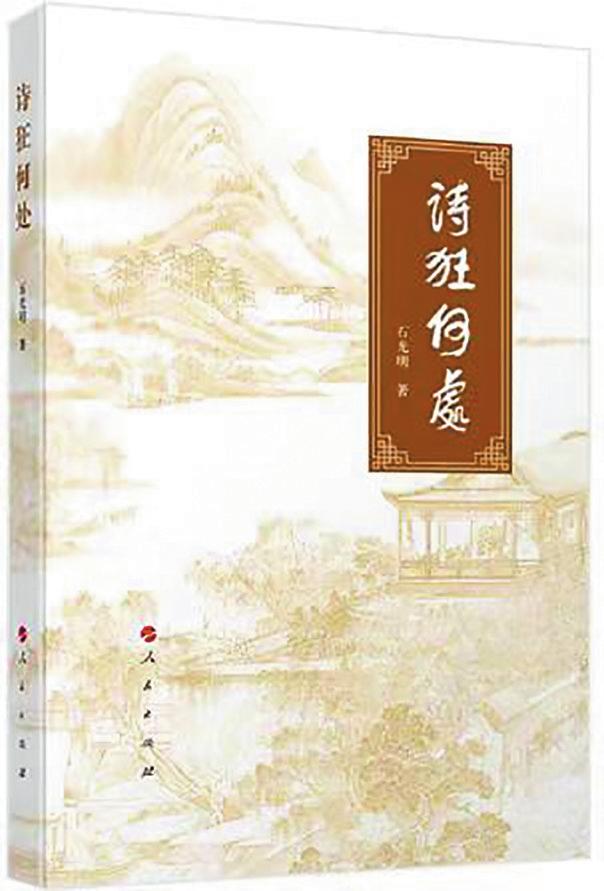刘绪义
在秋天的午夜,我泡上一壶黑茶,捧读起石光明先生的《诗狂何处》(人民出版社2023年7月版)。在这部散文集里,他愈来愈精到的文笔,他的盛世情怀,他的文化精神,燃起了他那绵远的盛唐乡愁。
一生“高开低走”的王勃,“含着金钥匙出生”的王维,“孤独寡援”的陈子昂,盛唐大手笔、江湖唱无奈的张说,活在唐明皇悔恨思念里的张九龄,喜欢出关玩月的王昌龄,史书中抑多扬少的崔颢,秋风驼铃里的边塞诗人,遗憾也能铸成诗碑的孟浩然,风月才子李白,“诗狂不知处”的贺知章,如此等等,盛唐诗坛中一系列耳熟能详的名字一一排队走过我的眼前,伴随着石光明的文字,也唤醒我沉睡多年的盛唐乡愁,许多熟悉的、陌生的风光,如穿越时光隧道一样,激起我无边的遐思。
《诗狂何处》是一部浸透着作者深厚学养和史识的学术散文。这种学术散文不同于曾经流行的历史文化散文,将个人情感与历史文化相结合,凭着宏大叙事与浓烈的想象来渲染个人情怀,文字看似壮美实则虚空无着,读完之后并无实质性的美的享受。当然,它也不同于那种颇受人喜欢的学者散文,适应当代传媒快餐式传播的需要,以短小的篇幅,讲述学界或学者的心路历程,回顾学术经历,纪念一段学术情缘,记载某种学术思考,展示某种人生思考,让学术走进大众视野。
石光明不在学界,也不受历史文化散文的框囿,他走出了一条新路,他的每一篇文章,都可以被看作是一篇学术讲座。《与君离别意》虽然是讲王勃,却展现了初唐四杰的另一面;《月明夜郎西》虽是讲王昌龄,却澄清了一段千年的误会;《总是风月无边》虽是讲李白,却展现了洞庭湖的无边风月。他的文字出入盛唐政治、文化、社会、文学、山水地理等方方面面,从庙堂之高到底层士子,从羌笛悠扬的边关到落叶满阶的江南,视野恢宏,触觉灵敏,从一代诗风的产生到转变,从诗歌的意蕴到诗理的内涵,从诗人的行状轨迹到诗思的兴寄怨叹,贯穿成一章起承转合的学术脉理,有考索,有梳理,有钩沉,有评析,时常给人以新的观点和新的启发。
以书名《诗狂何处》为例,人们想到“诗狂”,一般的指向都是大诗人李白,作者却写的是贺知章。对于贺知章这个“诗狂”的雅号,很多文学爱好者未必知道。作者正是带着“诗狂何处”这个疑问,帮我们从史料中钩沉出一个“诗狂”形象。36岁的贺知章一举成为浙江历史上第一位有史记载的状元,足以狂喜却淡定依然,一狂也;60岁以前,不争朝夕听天安命,少有微澜,二狂也;60岁以后,高位晚来,却依然放旷善谑,散淡风流,无复规检,三狂也;不以诗干谒,不旗亭画壁,不印诗集,随写随扔,四狂也;不怒不恼,没有政敌,亦无私敌,五狂也;金龟换酒,酒后骑马,醉态朦胧,滑稽欢谑,六狂也。有此六狂,完整地诠释了唐人眼中的“狂”,与我们所理解的“狂”,全然是另一回事。李白仰慕其“风流”,杜甫将其排“酒中八仙”之首,李林甫称其为“遥遥南斗边”的“汉疏贤”,唐玄宗亲自赋诗送其归乡,摆酒长安,百官送行。他自己呢?生怕别人不知己狂,还自号“四明狂客”。这恐怕是“狂”的最高境界。
作为一部散文集,其语言像很多采用学术散文笔法的纪录片解说词,优美而不失质朴,洗练而又沉郁,没有汪洋恣肆的情感抒写,却能传达出盛唐诗人真实命运、对诗歌艺术的深刻理解。没有故作解人的文人心态,却能在丰富史料中勾画出盛唐诗人的独特性格和情感世界,启人深思,给人启迪。
盛唐之盛,盛在一股气,这股气,令人不由自主想到李白之狂、杜甫之愁、王维之禅、王勃之慨等等。石光明正是以一种当今的盛世情怀去体悟千年前那个盛世的诗人情怀,因而作者与古人之间便自然产生了一种共通共情,在这个基础上,作者更能真切地理解古人,对其诗思与行状更有了一种时隔千年却恍惚同在一个时空的同情的交流,共同构筑起一种跨越千年的“乡愁”。这“乡愁”与其说是盛唐的,不如说是当下的。读者细品,就不由自主地滋生起一种与古人共通的强烈的文化自信。
美文之美,美在一股气。这股气,在文章就是魂,在作者就是骨。石光明长期浸润在唐诗宋词的神韵当中,显然已经将唐人风骨、唐诗魂韵内化于心,外化于笔,化为这一篇篇散文,月旦唐诗,品悟古贤,以其盛世的情怀书写了一种盛唐的乡愁,为我们精神生活增添了一份不可或缺的情感寄托,也滋养了我们当下盛世中国的一种文化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