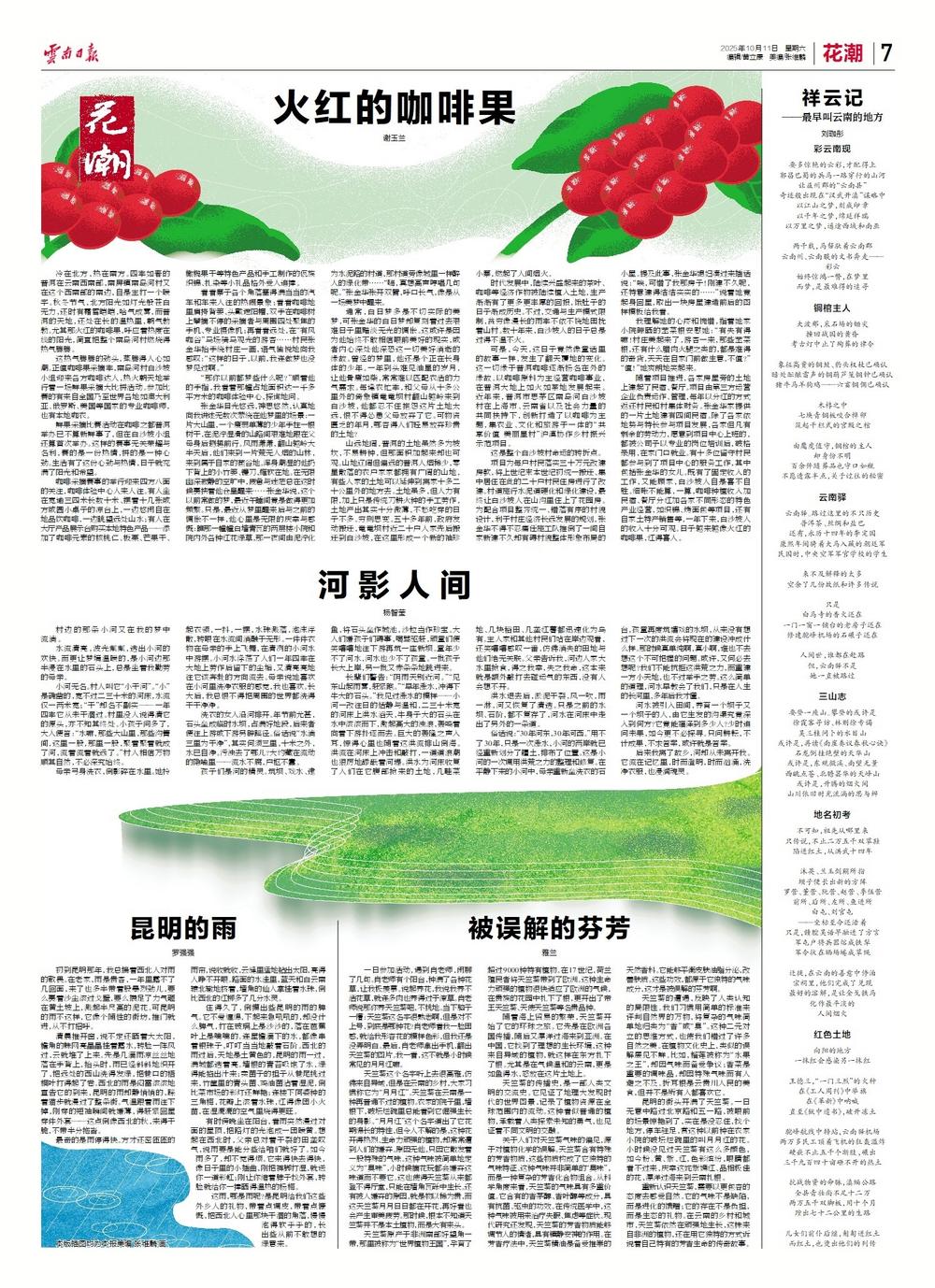杨智莹
村边的那条小河又在我的梦中流淌。
水流清亮,波光粼粼,透出小河的欢快。而更让梦境温暖的,是小河边那半浸在水里的石头上,总是坐着我勤劳的母亲。
小河无名。村人叫它“小干河”。“小”是确凿的,宽不过二三十米的河床,水流仅一两米宽;“干”却名不副实——一年四季它从未干涸过。村里没人说得清它的源头,亦不知其终处。小孩子问多了,大人便答:“水嘛,那些大山里,那些沟箐间,这里一股,那里一股,聚着聚着就成了河,流着流着就远了。”村人相信万物顺其自然,不必深究始终。
母亲弓身洗衣,倒影碎在水里。她拎起衣领,一抖,一摆,水珠溅落,泡沫浮散,转眼在水流间消融于无形。一件件衣物在母亲的手上飞舞,在清冽的小河水中游摆。小河水涤荡了人们一年四季在大地上劳作后留下的尘垢,又清亮亮地往它该奔赴的方向流去。母亲说她喜欢在小河里洗净衣服的感觉,我也喜欢。长大后,我总恨不得把周围的世界都洗得干干净净。
洗衣的女人沿河排开。年节前尤甚,石头垒成临时水坝,占满好地段,后来者便往上游或下游另辟蹊径。俗话说“水淌三里为干净”,其实何须三里,十米之外,水已自净。污浊去了哪儿?大约藏在流动的隐喻里——流水不腐,户枢不蠹。
孩子们是河的精灵。筑坝、戏水、逮鱼,将石头垒作城池,沙粒当作珍宝。大人们嫌孩子们碍事,喝骂驱赶,顽童们便笑嘻嘻地往下游再筑一座新坝。童年少不了河水,河水也少不了孩童。一批孩子长大上岸,另一批又赤条条地跳进来。
长辈们警告:“阴雨天别近河。”“见东山起雨雾,赶紧跑。”“早年涨水,冲得下牛大的石头。”我见过涨水的模样——小河一改往日的恬静与温和,二三十米宽的河床上洪水滔天,牛身子大的石头在水中滚滚而下,激起高大的浊浪,轰鸣着向着下游扑逐而去。巨大的轰隆之声入耳,惊得心里也随着这洪流排山倒海。洪流在河床上冲击和敲打,一道道浪潮也狠厉地舔舐着河堤。洪水为河床收复了人们在它腹部抢来的土地,几畦菜地、几块稻田、几垄红薯都迅速化为乌有。主人家和其他村民们站在岸边观看,还笑嘻嘻感叹一番,仿佛消失的田地与他们绝无关联。父亲告诉我,河边人家大水里抢食,得之我幸,失之我命,这本来就是额外敲打去碰运气的东西,没有人会想不开。
洪水退去后,淤泥干裂,风一吹,雨一淋,河又恢复了清透。只是之前的水坝、石阶,都不复存了,河水在河床中走出了另外的一条道。
俗话说:“30年河东,30年河西。”用不了30年,只是一次涨水,小河的两岸就已经重新划分了疆土,排布了位置。这是小河的一次调用洪荒之力的整理和修复。在平静下来的小河中,母亲重新垒洗衣的石台,孩童再度筑嬉戏的水坝,从来没有想过下一次的洪流会将现在的建设冲成什么样。那时候真单纯啊,真小啊,谁也不去想这个不可把握的问题。或许,又何必去想呢?我们不能抗拒这洪荒之力,而重建一方小天地,也不过举手之劳。这么简单的道理,河水早教会了我们,只是在人生的长河里,多年后我才懂。
河水被引入田间,养育一个坝子又一个坝子的人,由它生发的沟渠究竟深入到何方?它竟能福泽到多少人?少时追问未果,如今更不必探寻。只问耕耘,不计成果,不求答案,或许就是答案。
后来我离了故乡,河却从未离开我。它流在记忆里,时而澄明,时而汹涌,洗净衣服,也浸润魂灵。